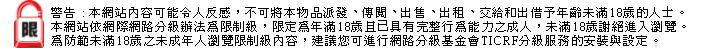【隱形守護者】 芳華(莊曉曼)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發布詔書,宣布接收盟國
的波茨坦公告,向中國無條件投降,這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線的勝利!是中國人民
的勝利!」
收音機里傳來了我無數次在夢中渴望聽到的聲音,然而,我尚未來得及有更
多勝利的喜悅,一陣軍靴踏地的腳步聲由遠而近,最終推開了家門,一張拘捕文
書立在眼前:
「根據上級文件,你被指控為漢奸,跟我們走吧。」
官兵毫無表情的將我銬住,帶上了車……
一路之上,盡是歡聲歌舞,老百姓每個人的臉上都掛滿了笑容,所有百姓都
自發的組織在一起,舉著自制的各種字幅、條幅、甚至還有搬著牌匾出來的,沖
著勃勃英姿的軍隊高喊著:
「歡迎凱旋!我們勝利了!歡迎你們回家!」
此情此景,我不禁有些感傷,我這個為了民族默默經歷了千難萬險,為了國
家榮譽與信仰屢遭蒙難的地下黨,卻只能被當做「漢奸」關在囚車中,連慶祝的
資格都沒有!
我背靠著汽車的鐵窗,目不斜視,生怕民眾的喜悅擊垮我偽裝的最後一絲堅
強!
忍耐了太久,經歷了太多,我無數次渴望這勝利的一刻,可當這一刻終於來
臨時,一切卻又那麼的不真實……
「進去!」
一名國民黨官兵將我一把推進了監牢,臨關門之前,透過門縫,還惡狠狠的
罵了一句:
「當什麼不好,非得當漢奸!」
隨後「咣」的一聲,鐵門緊鎖,也將我那顛簸蕩漾的心緒,重新按的死死的
……
「肖途?」
監獄中響起了一個熟悉的聲音。
我擡眼望去,竟然是亞輝通訊社的蔣社長!
原來,亞輝通訊社被國民黨抄了,而蔣社長的老婆,竟然偷了他早早預備的
船票,跟一個寫詩的跑了,無處可逃的蔣社長也就理所應當的被抓了進來。
此時的蔣社長一臉苦相,帶著哭腔問我:「肖途,我們會死在這兒麼?」
我此時根本沒有安慰他的心情,長嘆一聲:「哎,也許吧,我也不知道…
…」
「哎呀……這哪是人呆的地方啊……」
蔣社長正哭著,監牢的鐵門再次被打開。
「肖途,出來!」一名軍兵指著我,大聲喝道:「長官要見你!」
我帶著手銬,被這位官兵一路押著,走到了一個無人的走廊,一個窈窕人兒
此時正倚著墻,看向我的方向!
是她!
是曉曼!
那個一直在我心頭縈繞不斷,那個激勵著我不斷前行的女人!
「肖先生,好久不見!」莊曉曼離開墻壁,一臉微笑的看著我,同時對我身
後的人使了個眼色,押送我的官兵轉身離開了。
「莊曉曼?」這句不可置信的疑問脫口而出。
莊曉曼走到我身旁,將我的手銬打開,輕輕說道:「辛苦你了。」
看著她的一舉一動,今天所受的一切苦難,那些懸在半空飽受煎熬的委屈,
此時都落了地。
我該說些什麼呢……
面對著這位一身國民黨勁裝,身形標致的人兒,我有無數的話想說,但千言
萬語到了嘴邊,卻又不知從何說起,唯有一聲輕嘆,緩緩說道:
「難得,還能再看到你。」
這,恐怕是自上次與曉曼一別之後,幾年來從我嘴里說的第一句實話吧。
莊曉曼嘴角輕挑,用著她獨有的勾人聲線,溫軟的說:
「肖先生是怪曉曼沒有早點來看你?」
聽她這麼一說,心中倒是真的有些酸了,我輕聲一笑,不置可否……
「這次回來幾乎什麼地方都去過,就是沒來看望肖先生。」
說著,莊曉曼額頭微垂,皎潔的目光有些不好意思的看向我的胸前,嘴角有
些小得意的笑著,或許她是為了化解某些尷尬?
曉曼擡起帶著白手套的手,整理了一下我的領帶,繼續柔媚的說:
「別怪我,『胡峰』很忙的!」
我聽了這話,有些驚訝的問:「你是怎麼?」
「是第二號讓我來救先生的,上次分別後,我才知道我多了先生這麼個『情
人』。」
說道「情人」二字,莊曉曼收回整理我領帶的手,眉目低垂,一臉淺笑。
我看著她的姿容,心中不免感慨,當年那些同生共死,盡管難以忘懷,但竟
不及曉曼的一抹笑靨來的刻骨銘心!
此時的我,該表達心中所想麼?我……有資格麼……
盡管只是短短幾秒,但我的心緒卻已驚濤駭浪。
或許……我們這種人,不配擁有愛情吧,配麼?哎……
「回軒駐輕蓋,留酌待情人。」我忽然想起了鮑照的這句詩,念白出來。
我看著曉曼那略帶著邪魅的淺笑,居然有些動容,我知道這詩或許有些曖昧,
依然不敢傾吐心聲的我,話鋒一轉,對面前的曉曼繼續說:
「這句詩里的情人,泛指天下有情之人,而非男歡女愛,我認為,憑借我和
莊小姐這過命的交情,叫一聲『情人』,又有何不可。」
莊曉曼聽後,臉上的那一絲動容立刻消散,邪魅的笑容更深了,擡起頭來,
幽幽的說:
「先生什麼時候變得這麼能說會道了。」
我註視著她的雙眸,不知為何,眸光之中,竟帶著絲絲怨忿,是我的錯覺麼?
莊曉曼鼻息輕哼,繼續帶著笑臉說道:「也罷,三年前我在鄉下養好傷後,
第二號把我送去延安學習,又送我去國軍潛伏……第二號讓我轉告肖先生一句話,
在迎來最後的勝利之前,還請肖先生耐心等待,有時候,屈辱的活下去比悲壯的
死去,更需要勇氣!」
「謝謝你,曉曼!」
「臨走之前,還有什麼能為肖先生效勞的麼?」
「你……這就要走了?」此話一說,我就後悔了,經歷了這麼多年的磨練,
我竟然還會有如此失態的時候,真是該死。
莊曉曼仿佛看出了我眼中的不舍,眉頭輕蹙,但旋即恢複正常,一臉狡黠的
柔聲問道:
「怎麼?先生,舍不得我?」
「我……」當此非常時期,絕不能放任自己的情感,我有些慘然的一笑,說
道:「給我來支煙吧。」
「呵呵呵,」曉曼那標誌性的笑容再次鉆心剜骨而來,她取出煙,劃著火柴,
一邊為我點煙,一邊說著:
「肖先生的煙癮,還真是大呢!」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閉著眼睛息心感受,煙帶來的麻痹效果微乎其微,腦海
中縈繞的,全是莊曉曼的一顰一笑,盡管佳人就在跟前,卻仿佛隔著萬仞深淵,
讓我無從接觸,也不敢接觸……
「有句話,放在我心里很久了!」莊曉曼忽然說道。
「嗯?」我有些疑惑的看著她。
我竟然驚訝發現了一抹在莊曉曼臉上,從來未曾出現過的深情!
莊曉曼低著頭,雙手放在胸前,慢慢向我靠近,仿佛耳語一般的說:
「其實我非常喜歡……」
曉曼又向前邁了一小步,她的腳跟已經與我的腳尖並齊了:
「非常……」
曉曼雙腳踮起,因為踮腳,那軍靴腳尖上的褶皺,竟然顯得格外的性感!看
著曉曼幾乎貼到我身上了,我的心無比緊張……
曉曼已經將嘴巴幾乎貼在了我的耳邊:
「非常……喜歡……潛伏,呵呵呵……」
莊曉曼仿佛作怪得逞的少女一般,看著面色倉惶的我,說道:
「之後,我會飛往臺灣執行任務,只能以後,請肖先生喝酒了,在那之前,
好好活著。」
說完這句話,莊曉曼過身去,帶著她獨有的妖嬈笑容,漫步離開,望著她的
背影,她的每一步,仿佛都踩在了我的心弦之上。
「在那之前,好好活著!」
嗯,曉曼,我等著你來請我喝酒!
我如是想道。
————————
之後三年多的漫長歲月,我都是在牢里度過,蔣社長從一開始的焦躁不安,
整日哭愁,變成了頹然任命,而我呢,身上已經臭了,臉色也變得蠟黃,但卻從
未放棄對生命的希望,腦海中一直回蕩著曉曼的那句「在那之前,好好活著!」
那時與莊曉曼的談話雖然僅僅五分鐘,但卻一直激勵著我,甚至不知何時,
竟超過了那份已經越來越看不清的信仰。
在牢里的這幾年,我時長懷念過去的日子,那時候,幾乎每個早晨,我都能
在上班時碰到曉曼,對視,沈默,擦肩而過……
為什麼當時沒和她多說幾句話呢,此時的漫漫長路,也能多一些回憶不是麼
……
哎,恐怕即便再來一次,我還是不能與她多說什麼,就好比三年之前在監獄
走廊,「回軒駐輕蓋,留酌待情人。」話都說到那種程度了,我卻依然緊緊繃著
情感,不敢宣泄,畢竟,我們都是習慣了離別與死亡的地下工作者,此時宣泄感
情,只會成了她本不該有的牽絆,我無法對她負責,又怎能輕易許諾呢。
她說她非常喜歡……非常喜歡……「潛伏」,哎,有那麼一瞬,我真的以為
她說的是喜歡我,哈哈,可笑……我真是可笑啊……
————————
1949年1月。
「叫到號碼的,出來!」監管監獄的國民黨官兵喊著:「38號,12號,
你,12號!出來!下一個,37號,42號,18號……」
蔣社長來到我的身邊,我尚在睡眼朦朧的狀態。
「唉?肖途?醒醒,聽說了麼?有不少人被拉出去秘密處決了!」
「什麼?」我驚訝道。
「哎呀……」蔣社長長嘆一聲,小聲說道:「國民黨現在節節敗退,只怕,
只怕馬上就要是共產黨的天下了!這老蔣要退守臺灣,現在在大肆清理我們這樣
的人,怎麼辦?肖途?」
「哎,別想那麼多了,能活一天是一天!」我轉過身去,閉上眼睛,假意睡
覺,不再理會蔣社長的絮叨。
此刻的我,腦海中再次浮現出了那個女人的音容笑貌,蔣介石要退守臺灣,
記得曉曼說過,她當時是去臺灣執行任務,也不知現在怎麼樣了,國內形勢一片
大好,她有沒有回來呢?有沒有恢複共產黨的身份呢。
想到她的身份,我不由得會心一笑,說起來,她現在才是「胡峰」啊,呵呵
……
想著想著,我再次睡著了……
「6號!」
一聲來自門外的大喊,打斷了我的睡眠,我是6號!
「6號!出來!」
我坐起身,接著微弱的光芒,看到那名喊話的軍官用槍指著我,再次喊道:
「6號,聽不見麼?出來!」
「肖途!肖途!」蔣社長看到我慢慢起身,臉上大驚失色,喊我名字的時候,
居然帶了哭腔:「肖途啊……」
沒辦法,我只能跟著他走,臨走前,看著哭喪臉的蔣社長,心頭悵然,如果
真的是帶我秘密處決的話,我這最後一面見到的熟人,居然是他……
官兵不客氣的將我推走,一直推到了監牢之外。
此時正值午夜,天空沒有半點雲彩,寒月當空,繁星閃耀,1月的上海,帶
著濕氣的涼風吹打著我襤褸的衣衫……
「別東張西望的,快走!」
身後的官兵又推了我一把!
我心道:押送我的居然只有一個人,就不怕有什麼閃失麼?
旋即我又一想:我帶著手銬腳鐐,他手里還有槍,哪會有什麼閃失……
沒一會兒,我被押到了一輛大貨車上,貨車的車廂門關閉,車廂中一片漆黑。
隨著貨車發動機的聲音響起,貨車慢慢啟動,越行越快……
「呲啦……」
一聲火柴劃著的聲音忽然響起,這車廂中居然還有別人!
借著火柴上的微光,我看到拿著火柴的粗糙黝黑的手指,沒一會兒,火柴點
燃了一盞油燈!
面前,坐著一位面色帶著滄桑的中年人,方形臉,瞇著眼,正仔細端詳著我。
「你……」
我正要張口詢問,那中年人擡起手掌制止了我,隨後說道:
「我在找一本名叫做《容齋六筆》的書!」
這一句話,仿佛在我腦海中炸開了一顆核彈!
「容……容齋……」
我咽了口唾沫,穩住情緒,生怕自己說錯:
「《容齋隨筆》只有五筆!」
「呵呵呵,」中年人呵呵一笑,說道:「肖先生,你好啊!」
「你……你好,你們是怎麼找到我的?」
「哎,先別急,肖先生,我還要問你一些問題,當年你的方老師是怎麼死的,
還記得細節麼?」
我心頭一凜,長嘆一聲,將當年的種種,都說了個遍……
隨後中年人又問道:「那麼……那位出賣你方老師的線人,是如何被抓的呢?」
「你是說趙忠義吧……」我自己都驚訝,這個名字我居然還記得這麼清楚:
「我們當時……」
我將那寫了四封地點時間不同的邀請信計劃,詳細的說了一遍,中年人非常
的滿意。
「呵呵呵,」中年人很喜歡笑,他從懷中取出一個檔案袋,將里面的文件取
了出來,遞給了我,同時收起笑容,一臉莊重的說道:
「胡峰同誌,歡迎你回歸組織的懷抱!」
「胡峰?」
我腦袋一陣眩暈,他們是怎麼知道的?我的那些有關胡峰的文件不都被燒了
麼?
我接過文件,第一頁,竟然就是我的入黨申請書!
「這些文件,是一位代號為『第三號』的地下工作者為我們提供的!」
這字跡,連我本人都有些瞧不出是仿寫的!但,字跡似曾相識!是她!只能
是她!方敏!
我緊緊握住我的入黨申請書,眼淚止不住的流淌著!
我穩了穩情緒,說道:「這位『第三號』,現在在哪?」
「這個我們就不清楚了,這是我們第一次接到這位同誌的情報,估計他還在
潛伏中,不過胡峰同誌不用擔心,此時戰事正好,也許,要不了多久,你們就能
見面呢!」
「嗯,對了,我們現在是去哪?」我問道。
「咱們在上海有秘密根據地,現在老蔣已經節節敗退,上海也很快要被解放
了,他們國民黨已經只顧自保,而肅清地下黨的工作也變得松了許多,我帶你去
那邊,說起來,我們剛剛抓獲了一個很有意思的間諜,居然也自稱『胡峰』,呵
呵,若不是我們先一步收到『第三號』的文件,還真的上了她的當了!」
「什麼?」我大驚失色:「她……她……你們是怎麼抓獲她的?」
「呵呵,說起來你可能不信,她是自投羅網,此人自稱『胡峰』,直接來的
我們地下組織根據地,暗號對答如流,但卻對您『胡峰』早一些的功績含糊其辭,
與文件上的內容大有出入!但你不同,你剛剛說的那些細節,比『第三號』送來
的文件還要詳實!」
我此刻已經無暇他顧,問道:「那位冒充我的,是一個女人麼?」
「哎喲?」中年人眉毛一挑,說道:「沒想到,肖先生竟然認識她?」
我心中篤定,就是莊曉曼了!她不是去臺灣了麼,這種時候,回來做什麼?
「她有說過她的名字麼?」
「她說她叫莊曉曼!」
果然!
中年人繼續說道:
「我們已經對莊曉曼這個名字進行了更進一步的探查,呵呵,很有意思,她
根本就是軍統的人,老早以前就是了,這次竟然敢冒充我們的英雄人物『胡峰』,
可見此女人的危險,我們經研究決定,今天淩晨兩點就對她就地處決了!」
「什麼!今天?」
「對,」中年人看了看表,說道:「還有一個小時。」
「我……我能看看她麼?」
「當然,咱們還有二十分鐘就到了,莊曉曼應該已經被押到刑場了吧,說起
來,你這個真『胡峰』,的確應該見她一面才對。」中年人說到此處,敲了敲貨
車隔板,對著前車廂喊道:「同誌,咱們換地方,直接去耿家老院對面的黃浦江
邊!」
「好!」
聽到司機的回應,我的心慢慢平複下來,我告誡自己,要淡定,穩住心神,
此時此刻,我應當明白自己的處境,方敏作為『第三號』提供的文件,恐怕組織
也沒有完全相信,而莊曉曼在延安學習並加入我黨,都是以『胡峰』的假身份,
也難怪這些組織的人對她記恨!
而我這個『胡峰』的身份,如果回到組織的第一件事就是為一個軍統工作者
平反,恐怕也沒什麼說服力,若我此時貿然為莊曉曼證明,說不定這眼前的中年
人連曉曼都不讓我見了……怎麼辦呢?
我思前想後也沒什麼主意,就這麼如坐針氈的過了半小時,車停了,我走下
車,聽到我手銬腳鐐的聲音,中年人哈哈一笑,說道:「哎,胡峰同誌不要見怪,
我居然忘記給你取下鐐銬了,說著,不知從哪弄來的鑰匙,給我打開了手銬腳鐐,
我再次恢複自由。」
幾位同誌迎了上來,中年人為我們做了介紹,那幾位同誌一臉慨然的沖我行
禮:「胡峰同誌,歡迎回到組織!」
「莊曉曼呢?」我直接問道。
「在那邊!我帶您過去!」
我們來到了黃浦江邊,終於,我再次看到了她!
「曉曼!」
「肖……肖先生?」
莊曉曼擡眼看向我,眼神中充滿著驚喜!
「胡峰同誌,就是她,冒充你的身份,我們查明了,她竟然是國民黨的人,
這些年冒充您的名義,不知暗地里做了多少有損組織的事情,哼,經組織決定,
我們正要處決她!」
我身後的一位小夥子端著槍,義憤填膺的說著。
救我的中年人擺了擺手,制止了那個小夥子的話,隨後從遞給我了一把手槍,
說道:「胡峰同誌,今天這個任務交給你了,處決了她,我們也正好給你記上一
功,胡峰同誌回到組織的第一天,就親手解決了一位軍統老牌間諜,堪稱傳奇啊!」
我知道,這中年人是在試探我,莊曉曼的性命他們自然不在乎,如果我不開
槍,恐怕,我身後的這些憤慨的年輕同誌,連我都要一起斃了!
我拿著槍,走到莊曉曼身邊!
她還是那麼的美,此時再見,一如當年,同樣是一身軍統局的制服,明眸皓
齒之間,揚著勾人心魂的淺笑。
「肖先生,」莊曉曼說道:「能死在你的手里,恐怕老天是對曉曼最大的關
懷了吧,肖先生,動手吧。」
「曉曼,你為什麼回來?」我擡起槍,將槍口抵在了曉曼的額頭。
「呵呵呵,」莊曉曼笑著說:「為什麼?有那麼重要麼?我借用你的身份這
麼多年,今天由你殺了我,挺好的,你救過我,我欠你的!肖先生,以後想到我,
也能為我流幾滴淚吧?」
「真的要我動手麼?」
「還有別的選擇麼?」莊曉曼眼眶略帶濕潤的看著我:「動手吧,趁著我還
堅強!」
我望著她的絕美容顏,又看了看她身後漆黑一片的黃浦江,淒然一笑,說道:
「為什麼,不能多想一種辦法呢!」
說完,我一把將莊曉曼攬在懷里,與她一起縱身跳進了黃浦江!
「開槍!別讓他們跑了!」
在寒冷的水中,我聽到了岸上有人呼喊,隨後便是一陣槍聲……
一顆子彈,打中了我的大腿,劇痛傳來,我忍不住張嘴,江水立刻灌入,我
整個人便失去了意識……
——————
「嗚————」
輪船的轟鳴聲,讓我幽幽醒轉,我正躺在一張軟床上,剛要動彈,大腿傳來
劇痛,讓我跌回床上。
「噢喲,肖先生醒了?」一個帶著濃濃上海口音的男人聲音傳來。
我循聲望去,熟悉的面龐映入眼簾!
「徐先生?」
「哈哈,是我,放心,你的腿上的子彈已經取出來了,因為失血過多,你昏
迷了兩天了。」徐先生笑道:
「沒想到啊,你我二人當日共通殺入敵營,同生共死,再一別,許多年過去,
竟是在此處相見吶。」
「這……這是怎麼回事?」
「哈哈,」徐先生笑道:
「如今大上海已不是我的天下了,共產黨眼看著就要打來,我們只能溜之大
吉了,哈哈,前些天我雇了私船,趁著天黑,淩晨出發,沒想到竟從江上救下了
你,肖先生當年幫我打回興榮幫,今日我們兩不相欠了!這兩日你一直昏迷,餓
壞了吧,我去給你準備吃的。」
「徐先生,曉曼呢?」這是我最關心的事情。
莊曉曼當年沒少在徐先生的大上海夜總會進出,徐先生肯定是認識她的,如
果我們在一起,徐先生應該會救的吧?我中槍了尚能活命,她……她應該也……
徐先生看著我擔心的神情,微微一笑,沒有答話,正在此時,船艙的門開了。
只見一位穿著軍統制服的曼妙身影站在門口,雙手抱在胸前,翹著一只腳,
肩膀和腦袋斜靠著門框,正一臉笑意的瞧著我,陽光從門外照射進來,為她曼妙
的身姿打上了一層光暈!
這一定是我這輩子,見過最美的畫面了!
——————
三個月後,我們依然在船上,航行在無邊無際的大海中。
我的腿傷已然痊愈,從徐先生那里得知,我們此行的目的地是美國舊金山,
因為要避開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的勢力,所以這艘私船從黃浦江到長江,再到東
海,這一段路程走了不短的時間,現在路程已過大半,很快就能到美國了。
我打開船艙,來到甲板,看到莊曉曼正望著遠方的海面出神。
告別了以往的日子,莊曉曼自然不能再穿軍統的衣服了,還好徐先生的船上
並不缺衣服,今日的她,穿了一身淡藍色的旗袍,上身披著一件深棕色圍巾,長
發盤在腦後,海風掠過,將她的旗袍下擺高高吹起,修長的美腿在肉色絲襪的包
裹下,性感撩人。
恍惚中,我的思緒竟回到了多年前的酒吧,她與我初次共飲,最終留給了我
一枚子彈!
我緩緩走到莊曉曼身邊,莊曉曼並沒有看我,而是繼續盯著海面,口中說道:
「肖先生,我在此出神已久,你可知我在想些什麼?」
她的語調又恢複到了往常的勾人心弦。
我輕輕一笑說道:「肖某不知莊小姐在想什麼,但肖某此時,腦海中回蕩的,
都是當年在酒吧,你我第一次共飲時的旖旎時光。」
「旖旎時光?」莊曉曼輕聲回道:「肖先生,還真是會用詞啊,呵呵呵,看
來我們一如既往的默契。」
「怎麼?莫不是,我們想到一處去了?」
莊曉曼點了點頭,繼續望著大海,再沒說話,耳邊盡是海浪的聲音。
良久,莊曉曼仿佛下定了什麼決心般轉過頭來,雙眼帶著一層我捉摸不透的
神情,望著我說:「可惜啊,此處沒有酒,也沒有槍。」
我望著她的雙眼,她雙眸閃動,似乎有一種情意即將傾撒而出,我點了點頭,
莊曉曼向前走了一步,靠的我更近了,眸光流轉,櫻唇輕啟,莊曉曼溫軟的念道:
「回軒駐輕蓋,留酌待情人。」
我聽著這句詩,看著眼前美人的眼眸,一時間竟有些醉了,只聽曉曼繼續說:
「這句詩里的情人,泛指天下有情之人,而非男歡女愛,我認為,憑借我和
肖先生這過命的交情,叫一聲『情人』,又有何不可?」
曉曼的聲音柔情百轉,重複著當年我說過的話,原來,這一切她都記得,我
輕輕的回複道:
「有句話,放在我心里很久了!」
莊曉曼聽到這句話,眼眸中泛起了星星淚花,但她卻有意控制,神色依舊是
那麼的淡然妖媚。
我目不轉睛的看著莊曉曼,慢慢的想她靠近,輕輕的說:
「其實我非常喜歡……」
隨後又向前邁了一小步,腳尖碰到了她的雙腳:
「非常……」
我低下頭,將嘴巴貼到她的耳邊,輕輕說道:
「非常……喜歡……你……」
我明顯感覺到,當最後的「你」字說出來的時候,她全身一顫,她動容了。
莊曉曼擡起頭,原本掛在她眼睛里的淚花已悄然滑落,她依舊強裝鎮定,但
聲音已經變得顫抖哽咽:
「肖途,你知道,我為什麼要回上海麼?」
「原本不知道,但現在我知道了。」
不由分說,我一把將曉曼攬入懷中,將她緊緊的抱住!
在我懷中的曉曼踮起腳,紅唇在我的嘴唇上輕輕一點,我看著她的嫵媚容顏,
看著她的深情款款,不能自已,用力的吻住了她,這一刻的擁吻,讓我緊繃了多
年的心弦終於放下,那些蕭索往昔,仿佛隨著凜冽海風,一散而空了!
我不知我們擁吻了多久,也不知我們是怎麼回到的船艙,我只知此刻佳人在
懷,軟床之上,我們彼此交融,無法自拔!
曉曼的長發已經散開,我的堅硬被她的柔軟緊緊包裹,曉曼的酥乳緊貼著我
的胸膛,我一只手撫摸著她的美背,另一只手緊捏著她的翹臀,曉曼的一雙長腿
箍在我的腰間……
伴隨著我的聳動,曉曼柔情百轉的呻吟,盡管有意控制,生怕隔壁倉的人聽
到,但這輕吟的聲音卻依舊撩動著我每一根敏感的神經!
不知纏綿了多久,我與曉曼一直緊緊相擁,不願分開,逐漸的,隨著情欲的
消散,我們彼此之間隱忍了多年的濃濃愛意,終於修得正果,再無遺憾……
——————
1972年,美國舊金山。
唐人街,此時的我已年近半百,曉曼與我有了兩個孩子,他們的身上已經完
全看不到我們當年的影子,畢竟,沒有經歷過我們的年代啊……
我因為精通日語,而曉曼精通英語,我們在一家報社從事著翻譯的工作,日
子非常安穩。
我們經歷了太多的波折生死,此時的安穩讓我們倍感滿足,不過,住在這家
店的一位老朋友,可就不這麼想了。
這家店是唐人街最正宗的中餐館,上海小吃尤其美味,店主是一位叫曉曉的
姑娘,她的養父,則是當年救了我和曉曼的徐先生。
三十年前大上海手眼通天的興榮幫幫主,如今要靠女兒經營的小餐館茍延殘
喘,他怎能甘心,這些年靠著手中的人脈,雖不及當年輝煌,卻也與很多大人物
都有了交集。
我和曉曼點了揚州炒飯,正等待著,一身廚師服的徐先生走了過來,手中拿
著一封信,他呵呵笑著將信放在我面前,說道:
「肖先生,這封信有意思了,發件的地址竟然是大上海夜總會,哈哈,那里
恐怕早就拆了吧。」
「哦?」我饒有興趣的看向那封信。
「嗯?更有意思的是恐怕是這收件人吧。」莊曉曼瞇著眼睛盯著信封說道。
我這才註意,一行英文地址之後,竟是三個娟秀的漢字「胡峰收」!
我震驚的拆開信件,一張照片掉了出來,那照片上的,是一位熟人,一位老
同學,或者,叫她『第三號』更為恰當!
照片中的方敏與一個男人手挽著手,站在一座陌生的橋上,面帶微笑。
我放下照片,再去看信,只見信中寫道:
胡峰:
一切可好?不用驚訝於我是如何得知你的身份與住址的,我自有我的方式,
照片上的那位,是我的愛人,一位美籍華人,從事記者工作,當初在我冒險將你
的所有文件寄給地下組織之後,就是這個人,冒死把我從軍統的手中救出來。
我過的不錯,不知老同學你怎麼樣了?快樂麼?幸福麼?
寄件地址的「大上海夜總會」,只是我隨便開的一個玩笑,那些日子,恐怕
胡峰同誌沒少去那里尋開心吧,呵呵。
我現在與我的愛人在美國洛杉磯安居定業,不知你此時如何?
據說與你一起逃往美國的還有一位軍統女子,看來你依然是艷福不淺嘛。
希望我們以後還有見面的日子,珍重。
-第三號
1972年5月30日
放下信件,我又看了看照片,一時間淚眼朦朧,隨後我握住了曉曼的手,彼
此相視一笑,一切盡在不言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