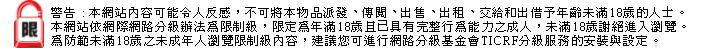金絲雀計畫 (加害者1)
第一個加害者
從我在「那個網站」發出「職缺」之後,有不少人慕名而來。就像所有的工作面試一樣,來的人良莠不齊,但我抱著像是選秀的心情一樣,給他們一些任務,看他們表現。所謂的任務其實說穿了很無聊。我那三隻金絲雀,在這以前只知道我的存在,我給他們那三個住戶的名字、作息表,清楚界定可行與不可行的時間,讓他們自由決定要溝誰、從誰開始。因為她們三個已經被我「處理」好了,利用她們來進行面試相當合理,但面試者則不知道。我在名單上加上了一些規則,表明在面試中及未來的每一天,觸犯這些規則的下場就是被踢出團隊。
理由很簡單。因為犯罪的人越多,風險就越高。他必須足夠細心,有耐心,找到受害者的切入點,他必須夠殘忍,缺乏同理心,有殘虐的喜好,可以在侵犯女性的過程中達到快樂,並以此產生成就感。他必須有計畫,有方法,把女性攻陷之外,他要能收服女性,把她們都困在牢籠裡,他更要有一個遠大的夢想,要創造沒有女性能夠守住貞操的世界。因為,這正是我對女人復仇的極致,我對汪思涵復仇的極致。我常常一邊強姦汪思涵,一邊告訴她我那邪惡的計畫
這一切在短短的一番對話跟介紹中都完全看不出來,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讓我看看他們的能耐。但是他們在進行進一步面試之前,為了保險起見,我還是進行了性病檢查。檢查方式簡單粗暴,抽血並且脫褲子,陰部沒有異樣,血液樣本檢驗正常,才成為合格面試者,可以參與面試。面試者中不乏性病患者,我這個保險確實有發揮一些作用。
這些面試的人大多數都是失敗者,失敗者們對我而言並不重要,甚至連花時間去記憶他們的名字都不需要,然而我還是很樂意為大家書寫這些失敗者的故事。
第一個失敗者,就在我攻陷張瀅彤的隔天找上我。通過性別篩檢之後,我就讓他開始工作。他先去按許芃的電鈴,跟她說了幾句話,隨即他就把許芃推進去,壓在沙發上,手伸進去她的裙底,開始玩弄起來。許芃一開始還有所抵抗,但是當他的手伸進她的裙底以後,許芃就陷入了男人的淫戲之中無法自拔。他用手指摳弄她的陰蒂,並把手指伸進去來回戳動。然後他抱著許芃的頭,讓她的口舌為他服務。我看得血脈賁張,把汪思涵叫過來,粗暴地使用者她的嘴巴。
這個面試者在許芃的表現獲得了我的好感,然而他對江曉芸跟張瀅彤的表現卻不盡人意。他埋伏在樓梯間,趁江曉芸回家的時候把她拖進維修通道姦淫一陣,他沒有意識到那維修通道沒有上鎖,更沒有進一步發現那維修通道沒鎖,可以潛入她的房間內。當他在維修通道,擺動著腰部盡情地姦汙江曉芸的時候,我暗自把他的名字從面試者名單中劃掉。然而他對許芃的作為讓我相當喜歡,所以我把張懷剛下藥之後,招待他跟我一起強姦張瀅彤。
三個女性之中,張瀅彤是崩壞得最徹底的。自從張懷剛強姦她之後,希望的燈火在她的眼中不再閃爍,不管是張懷剛或是我,或是面試者,任何人把她的裙子掀起來,陰莖掏出來,插進那柔嫩年幼的穴裡,她都沒有抵抗,哪怕是嘴巴說出「不要」都沒有。她讓自己飄在無邊的海裡隨波逐流,不求救,也不掙紮,只是那樣飄著。身體的感覺讓她在舒服的時候發出淫蕩的聲音,她也不忍耐,隨著快感輕聲地呼叫著。她覺得她已經無法再提起勇氣去抗拒這個世界對她釋出的惡意,如果讓這些男人做完想做的事,至少,他們會早一點結束。
張瀅彤是第一次被二個男人插入口腔跟性器。這讓她非常不舒服,但是沒有多久,她就學會用嘴巴去取悅那較小的肉棒,以免那巨大的龜頭插入她的喉嚨。我們在她身上盡情地發洩,然後任由她癱軟地躺在精液裡。
我讓這個面試者滿足之後,就讓他離開。他離去之前,我告訴他,如果對這些女人有興趣,他可以選擇來當個住戶。
「我會來的。」留下這句話,他就離開了。
第二個面試者相較之下,雖然有著敏銳的觀察力,但行動力不足。他發現了通往江曉芸房內的維修通道,也發現了許芃那自慰的壞習慣,但是他完全不知道該如何靠近這二個女人。我在面試的一週後,告訴他,他不符合我要的條件。
之後又有二個面試的失敗者,也對這三個女孩進行了不同程度的侵犯或羞辱,這個過程有相當程度的娛樂效果,但終究不是我要的人。我喜歡看這三個女人時不時就被陌生人強暴。這個面試的過程給了我許多我要的喜悅。張瀅彤,就是我理想的女性模樣。在此之後,有許多女人以張瀅彤為樣本,身體、心靈、精神支柱都徹底羞辱後,墮落到淫慾的深淵中,再也沒有哪怕是一絲的掙紮。
第五個面試者,則是我第一個加盟的夥伴。他是個金髮粗壯的男人。他的身體經過鍛鍊,身上的肌肉線條粗獷,身上有多處刺青,坐過多次牢獄。
「我叫王金南。」
「外國人?」我看著他的性病檢查報告,上面的簽名跟他說出的語言截然不同。另外他也把他過往的經歷寫得相當詳細。他是個「清道夫」,負責處決一些背叛組織的人,包括侵犯對象的女性關係人,如妻子、女兒,或本人後殺掉。他來面試的理由,只是想換個工作。
專業人士,我喜歡。
「是的,我是俄羅斯人,我的名字是威斯多夫.基利南斯,王金南是我的中文名字。我住在中俄邊境,從小就會說二種語言。」
我把三個金絲雀的資料給他。「你的面試題目是,一個禮拜以內調查她們,並且上了她們。這是她們的資料。」
「好。」他簡短地回答。「一個禮拜,三個人?」他看了看,把資料退給我。
「把精液射在體內。你不留著?」我疑惑地看著他。
「我記住了。」他的眼神尖銳。「你的任務並不輕鬆。」
「時間就這麼多。」我聳肩。
威斯多夫的行動非常老練。他的第一天,就發現了所有我留給他的線索,包括:三人屋子外的連結通道沒鎖,可以潛入。他也測試了另外一邊,知道只有這三人的暗門是特地被打開了。他趁江曉芸不在潛入了她的屋子內,看見了她那本淫穢的姦淫雜誌,知道她常常被脅迫姦淫的事實。他又潛入張家,發現了張懷剛的攝影機,那台攝影機現在已經明目張膽放在客廳,張懷剛跟她女兒搞上的時候,也拿出來拍攝助興。他看了錄影帶,播映的時候特別注意秒數,看完之後倒轉到對應的秒數,關閉。細心,我很喜歡這一點。這部父女交媾的影片倒不是我刻意留給他的線索,他完全沒有遺漏。他又潛進許芃屋子旁的維修通道,側耳傾聽屋內的動靜。許芃整天都在家,他在那裡安靜地等待著。屋內有隔音設備,維修通道充滿了機械跟排水的噪音,要知道屋內的動靜相當困難,但這沒有難倒他。他使用特殊的軍事裝備,一種感熱儀器,完全捕捉到許芃的動靜。由於我在許芃的兒子不在的時候無間斷供應著春藥,她在下午時心癢難耐地待在房間裡自慰。威斯多夫此時身手矯健地探進屋內,觀察屋內擺設,搜索了他兒子的房間跟客廳、浴室,除了半掩門的主臥房以外,整個屋子都檢查過,就離開現場。他並沒有被誘惑,只是小心仔細地迅速了解他的獵物。
但他沒有發現屋內燈具的感光攝影鏡頭。正當我這麼想的時候,他正好拆開一座燈具,看著那攝影鏡頭,拿起手機撥了一通電話。
我的手機震動,接起來,就聽見威斯多夫的聲音。
「你在看著我嗎?」他邊問,邊帶起無線耳機,把手機收起來。
「是。」我回答。
「我住的地方也要監視嗎?」他問。
「是。」我答。
「這是工作條件嗎?」他又問。
「是。」我回答。
「我能保有一部分的隱私嗎?」他再問。他的動作並沒有停止,正在客廳拆卸音箱,他在找隱藏麥克風,把音箱拆了下來,仔細搜索。但是音響麥克風隱藏得很好,音響本身就是麥克風,這點他倒沒有意料到。
「很抱歉,不能。我們確定同夥之後,我會保證分享我全部的情報給你。我的住所跟你的住所一樣透明,這是這裡的規矩。」我回答。
「我知道了。」
威斯多夫帶來的箱子還有一個,他把它對著鏡頭打開,那是三把不同尺寸的槍。手槍、衝鋒槍、狙擊槍,至少,不同長度的槍管是很清楚的。槍枝拆成零件放在箱子大小不一的凹槽裡。那些凹槽顯然是依照槍枝零件的尺寸去設計的,是為了這些零件在運送的過程中不致碰撞。凹槽裝在零件的箱子有三層,他把手槍組裝起來,又穿起槍套,把槍套在腰際。「如果你敢洩漏我的情報,我保證會來找你。我現在要開始行動,這槍只是個保險。」他說。
「我保證,你的隱私只有我們同夥的人知道。」我回答。
接下來威斯多夫就在電話中對我報告他的發現。除了先前他在三個地方收集的情報以外,他總結他的觀察。「三個女人都受到不明人士威脅,被迫提供性服務。」他說,「我相信那個人就是你。」他的觀察真的相當犀利,連許芃被我灌食春藥都發現了。我對於他的觀察力非常佩服。
「是我。我還不認識你們,讓你們去襲擊沒有被威脅的女人實在危險。不過對你來說,即使是沒有威脅過的女人你也沒問題的吧。你對這些可以任意玩弄的女人還有興趣嗎?」我問。
「工作就是工作。」他回答,關上手機。
威斯多夫的裝備很齊全。他戴著夜視鏡,經由維修通道潛入江曉芸的房間,此時她正戴著眼罩,在房內裸睡。威斯托夫接近她,脫下褲子,搓揉陰莖,讓它挺立起來,就直接躺上去,把他的陰莖插進江曉芸的下體。他並不愛撫,也不享受,就只是直進直出地,連做愛也說不上,機械式地射精後離去。
他回到房間,開始脫槍。我打電話給他。
「你不享受一下嗎?」他接起來,就聽到我的第一句話。
「工作就是工作。」他解釋。「你只是要看我能夠多快幹了她們,不是嗎?」
「沒錯。」我回答。
「你希望我挑逗她們嗎?」他冷靜地問。
「不需要。我喜歡看你今天糟蹋她的樣子。」我回答。
「面試明天就會結束。」他接口。
「我很期待。」說完,我便掛了電話。
威斯多夫的習慣跟我一樣,他是個裸睡的男人。他掛了電話就寬衣解帶,洗完澡爬上床蓋上棉被睡覺。
我看著露出半頭的金髮外國人,嘴角泛著微笑,然後我也離開監視室回房就寢。
這一天我特別興奮,躺在床上遲遲沒有入睡,突然性起就把汪思涵壓在我的跨間。汪思涵伸出她的舌頭,軟綿柔膩上下順舔著我的陰莖,直到我沈沈睡去。睡眠中,突然腰際一陣酥麻,熱烈的精液射在汪思涵嘴裡,她才完成晚上的工作,被允許睡覺。
隔天一大早,我在八點時分舒服地醒來,汪思涵正在舔弄我的陰莖。我有可能會起床打晨砲,她必須要在我起床的時候把陰莖準備好,如果她沒有做好,就會遭受我的懲罰。我的懲罰是粗暴而且殘忍的,在她的餐點上排泄後逼她吃下,或是把她綑綁起來,先用指甲用力地刮出血痕,等它發炎後再撒鹽後幹到射精,而她之所以不敢反抗,是因為我威脅她,如果她敢反抗,我就把她綁起來,讓她跟我養的緬因貓交配。貓的陰莖是有倒鉤的,巨貓的陰莖插在人的穴裡面會刮出無數的碎肉。一般的女人可能會有所懷疑,但汪思涵知道我為了她,甚至連其他女人都敢侵犯,就是為了讓她看著這一切來報復她,她知道我說到做到,加上那包冰毒還在保險櫃裡隨時可見,即使我不督促,她也不敢違背我的命令。
我來到監控室,威斯多夫已經醒來,正在做運動。他赤裸著身體,全身的肌肉粗大而健壯,但皮膚表面沒有醒目的血管,這一幕讓女性瞳孔放大,即使是男性觀看也不至排斥。他的體能保持得非常好,正在做臂力訓練,二隻手撐住把全身挺起。運動結束後,他甩著陰莖進入浴室洗澡。汪思涵看見這個男人,害怕得躲遠。
「躲什麼?這個從今開始男人會跟我們待在一起。」我轉頭說。「我可沒打算讓妳當個烈女。」我看著汪思涵。她不被允許發問,只是抿著嘴看我。
威斯多夫盥洗完畢後穿上衣服,戴上槍,離開房間。
他去拜訪許芃。透過我提供的作息表,他知道她兒子已經出門,直接去許芃單位門口按電鈴,跟她說了幾句話。我從走廊的監視器看著二個人,許芃聽了一句話後露出驚訝的表情,隨即二個人就進入屋內。威斯多夫仍然沒有多餘的動作,讓許芃坐在沙發上,把雙腳打開。許芃穿著連身洋裝,長裙及地,那寬鬆的裙襬下仍然是赤裸的。她坐躺在沙發上,雙腳大開,威斯多夫再度掏出他的陰莖,跟前一晚一樣把它摩擦到粗硬,就壓在許芃身上。
畫面是反差相當大的。威斯多夫機械而粗魯地挺進,一下又一下地,有節奏地,重壓、重壓、重壓,緩慢而深地插入。許芃卻像是全身都觸電一樣擺動著軀幹,嘴巴張大,舌頭撩動,全身脹紅。這個組合非常特別,只見威斯多夫大約撞了二十幾分鐘,許芃就洩了。威斯多夫持續著穩定的節奏,臀部粗曠而有力地挺直,每一下都強而有力地從洞口插到深處,許芃就像我當初把玩的那樣,高潮時癱軟著,威斯托夫則毫不留情地持續穩定地撞擊,沒多久許芃又再度洩了。
這次威斯多夫花了將近一個小時,就這樣機械式地撞擊直到最後一刻,腰部緊壓在許芃的陰道上,深深地噴射完畢後,就拔出來,穿上褲子,轉身離去。
這個人很有意思。我看著躺在沙發上,像是被電擊棒電過一樣抽蓄的許芃,露出得意的微笑。
威斯多夫直到張瀅彤回來以前都不在大樓內。他跟著張瀅彤進大樓。他跟著張瀅彤進電梯,出電梯,走到她的門口。張瀅彤對這個跟蹤犯並沒有反應,彷彿他不存在似的。她開門,他跟著張瀅彤進到客廳,張瀅彤進去之後直奔客廳,彎腰雙手放在茶幾上,屁股朝向威斯多夫,威斯多夫掀起她的學生裙,掏出陰莖搓揉使它變大,就抱著她的屁股挺進著。這又是另一幅奇妙的畫面。張瀅彤完全沒有配合的動作,威斯多夫機械地抽插,二個人像是做愛機器一樣,一個靜靜地等待著對方射精,一個持續地挺進腰部。我看了十分鐘,這二個人也沒換動作,也沒換節奏,威斯多夫雙手抱著張瀅彤的腰臀處,不停地把陰莖插進去。這次也維持了四十分鐘左右,威斯多夫把龜頭頂到深處,開始射精。
結束後,威斯多夫離開張瀅彤的單位,上來找我。我在會客室等他。
「面試完成了。」他說。
「我知道。」我看著他。
「我合格嗎?」他問。
「非常合格!」我笑著對他張開雙手,示意他坐在沙發上。
「我對女人的性愛是處決式的。」威斯多夫坐下後說道。「很抱歉我無法做得更好。」
「處決!」我燦爛地笑了。「這就是我要的!女人就是用來射精的,她爽不爽不是我關心的。我們的工作就是強制打開越來越多的女人的大腿,對她們處決!我喜歡這個詞。沒錯,這裡的女人就是要用來處決的。」我說。「你是個完美的夥伴,基利南斯先生。我們就是要對這棟大樓的所有女人執行處決!你的面試非常成功,唯一的問題是,你願意讓我僱用嗎?」
「我正是為此而來。」威斯多夫看著我。
「很好,我們要繼續聚集更多人。」我笑著搭著他的肩。「現在,開始工作吧!」
我引他進入監控室,讓他看見我的監控系統。由於發現了攝影機,他對於這裡的設備並不意外。但他沒有想到這裡還有另一個人,赤身裸體捲在沙發上的汪思涵。
威斯多夫對於其他女人都沒多看一眼,但是卻仔細地盯著汪思涵。
「請別把她當人看,基利南斯先生。她的功能就是用來幫你射精的。我只有晚上睡覺的時候會把她帶走,其他時間,誰對她做了什麼我並不在乎。對了!請你對她執行你那個處決式性愛吧!她是個喜歡粗魯的人,請你執行的時候盡量粗暴一點!如果她不聽話,就做些什麼讓她聽話!」
威斯多夫往汪思涵靠近,看見健壯又高的俄羅斯特務往自己走來,汪思涵嚇得往後逃跑,但是威斯多夫很快就制伏了她,把她的手壓在背後,像是用手銬逮捕一樣壓在牆上強迫地機械式地挺進。汪思涵隨即發出像是幼狗一樣的呻吟聲。
「以後她就是你們的打卡鐘了!你們上班的時間就插進去以後用口紅在她的腰際寫時間!」突然想到一個好方法來折辱汪思涵,我笑著宣布最新的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