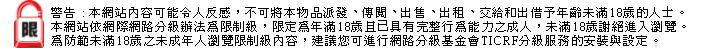綠光 1-5
序
映入眼簾,你會看到一個男性,1米6左右,只穿了一條綠色女式蕾絲內褲跪在地上。如果你再拉進來仔細看,你會看到他屁股里塞著肛塞,前面帶著一個金屬的貞操鎖,貞操鎖很小,只有3厘米,全密閉式設計隔絕了龜頭和空氣的接觸,僅僅只在尿道口開了一個小洞,使得雞巴看起來就像沒有一樣。
這是我。
我跪在那里,期待的的看著時間:下午5點。我知道我的女主人這個時候就快回來了……在等待中,我聽到一陣敲門聲,我激動地把門打開。
“怎麽樣?今天把房間收拾干淨了嗎?”
“收拾干淨了,就等著您檢查了。”我回答到。
我一邊說一邊幫那穿著OL職業裝的女性脫掉8cm的紅底黑色高跟鞋,然后麻利地仰面躺在地上。那女性駕輕就熟地把穿著80d黑絲襪腳底在我伸出來的舌頭上來回刮了刮——這是我倆長久形成的習慣,配合得特別默契。
進了屋,把包一丟,她仰頭就躺在了沙發上,右腳在沙發邊緣晃蕩。我連忙跪著爬到她腳邊,時而用舌頭上下反複舔她的絲襪腳底,時而吮吸她的絲襪腳尖。穿了一天的高檔高跟鞋的味道、日本進口的連褲襪的味道、還有她的40碼的腳本身散發的味道雜糅在一起,讓我欲罷不能。
服侍她的時光總是短暫的。從她5點下班到家后,她一般會在沙發上閉著眼小睡20分鍾,這個時間段需要用我的舌頭和牙齒愛撫她的腳底。然后,洗澡、化妝直到6點,中途需要我幫她拿衣服和“潤滑”。打扮好以后她就出門了,一般到12點才會來,或者不回來。
“輕一點!”她突然醒過來。
“對不起,我不知道這麽重……”我眼神躲躲閃閃。
她半坐起身,拉著我耳朵,使我不得不往前爬了幾步。“啪啪”,她正反手兩個耳光打在我嘴角:“我昨天難道沒說過?當耳旁風?”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只能一個勁地說對不起,她似乎聽煩了,起身,把我耳朵往上拉,低聲告訴我:“不懲罰你你是不會長記性的,三個星期吧。”
隨后,她走進浴室,反鎖了門。
我跪在浴室門前,等著我的主人洗完澡,洗完過后她還有很多用得到我的地方……
“進來。”我聽到了她在里面叫我。
我爬進浴室過后,女主人站在梳妝鏡前化妝。從鏡子里看,她人很美,是標準的古典東方美人,也不用畫得太濃,就可以迷倒衆生。秀發微卷,垂落香肩。
我跪在地上,把臉湊在了她的屁股中間,她把身子的半個重量都壓在了我臉上。我溫柔且費力地幫她舔著菊花和小穴。
因爲這三年的長久的訓練,所以我的舌頭特別靈活,她似乎也很喜歡我這樣舔。喜歡是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因爲她說男性的唾液能夠保證小穴和菊花的健康,使之舒適而不會太干。
我第一次聽她說這番話時,就問爲什麽要保證這兩個洞的溫潤呢?則被她賞了一耳光,她反問到:“那你覺得呢?你難道希望別人嫌棄我那里又干又硬嗎?”那時,我看她快生氣了,就趕緊埋下頭去舔她的腳拇指,一邊用余光小心地瞄著她的表情,她厭煩地把我踢開,三天都沒回來……回來過后,淡淡地告訴我那件事三個月別想了……
經曆此事過后,我再也不敢多問,但幫她潤滑這事就成了我倆約定俗成的日常工作。每天早晨她出門上班的時候會幫她潤滑一次;下班回來,在洗完澡出門前,我也會幫她潤滑一次;有的時候晚上和我一起睡覺時,也會要求我給她這樣做。每次潤滑的時間大概有10分鍾左右,她就趁這10分鍾的時間,畫好臉上的妝。在她畫好那一刻,我覺得她美極了。
隨后,我從臥室里帶來她的夜間裝備——吊帶絲襪和束腰,(這些束腰並不像中世紀那樣緊,而只做情趣用品)。絲襪是黑色的,束腰也是黑色的,甚至可以說,我的女主人所有的內衣幾乎都是黑色的。我還記得,在我追求她時,她問我喜歡什麽顔色,我說黑色,她告訴我說那她今后都穿黑色。從此,黑絲襪成了她的標配,春夏秋冬,我很少看見我她沒穿黑絲襪的時候。以致于到現在,一個櫃子都是她的黑色的絲襪、吊帶襪、長筒襪、連褲襪……
言歸正傳,在我的女主人穿好內衣過后,一般她會再穿上一個黑色V領露背包臀緊身連衣裙,外面再披上一件棕褐色或者深藍色的V領風衣。至于她是去哪,我還是不敢問的,如果她心情好,或許會自行透露出一點點去向,可能是party,可能是夜店蹦迪,也可能是酒吧。
最后,我雙手捧著高跟鞋,把頭深深埋在雙手下面,放到她腳剛好能伸進去的位置。在她的腳踝處,有一個金屬鎖鏈,鏈子上挂著我貞操鎖的小鑰匙——這是我釋放快樂的源泉。(我每天都能在服侍她的時候看到那個小鑰匙,但我是絕對不能用手觸碰,否則會遭受半年的鎖精和長達10小時的鞭打。當然,如果表現的好,她會讓我一個月撸管釋放一次。由于作爲奴隸,是不能太多耽誤主人的時間,所以我每一次撸管的時間只有兩分鍾。如果超過這個時間,不論我釋放與否,她都會把我的小不點放進冰水中,再把它放進冰冷的貞操鎖里。所以我尤爲珍惜這一個月一次的機會,一般一分鍾或者90秒,就會讓自己達到高潮。甚至有一次,在她給我開鎖的時候,僅僅是她的玉手有意無意的觸碰就讓我在鎖脫離雞巴的那一刻高潮了,自然,這個月就當釋放過了。有時,她會允許我在一邊逗弄自己的小不點的時候一邊吮吸著她的絲襪腳。而按照慣例,每一次射完,我都應衷心的“說謝謝主人”,然后用舌頭舔干淨射在地上的精液,最后主動求她幫我把鎖戴上……)
“希望主人幸福!”在她右腳剛剛穿上高跟鞋那一刻我低聲說道——這是一種固定的儀式,如果她心情好,或許會撲哧一笑,故意問我“幸福的性是哪個性啊?”也不要我的答案,就在我窘迫的表情中面帶微笑的離去。
砰!關門之后,又是我耐心等待的夜晚,如果12點她沒回來,我就自己睡了;如果回來了,可能晚上還能得到獎賞——幫她清理她小穴上的牛奶。
對了,我口中的女主人,是我三年前的女朋友。
第一章、子君
我與她是在大二的一個部門聚會上認識的,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從小縣城里面來的沒有見過世面的小夥子,1米6的身高,是人群中毫不起眼的那種。在聚會上,有一個長相清秀的姑娘映入了我的眼簾,比我稍微高半個頭的樣子,丹鳳眼,秀挺鼻,頭發披落腰間,穿著一件街頭常見的寬松T恤和牛仔褲,乍看是屬于青春運動類型的那種少女——盡管她不是特別讓人驚豔,但我細細端詳,我的心被她勾走了。
從那一刻我就打算追求她做我的女朋友:一來是因爲她並非特別漂亮,我在追求她的過程中不至于自卑;二來也是因爲她是我特別喜歡的類型。在經曆了三個月的辛勤送奶茶、送零食的追求過程中,她答應“嘗試”與我交往,但她說不希望我們這麽快就把關系公之于衆,所以我倆在學校從來沒有過親昵的舉動,也僅僅只是並肩走在一起罷了(也沒有牽手)。平時,我禁不住向室友炫耀,室友說:“一般般的女人,穿衣品味也不咋地,你是怎麽看的上她的。”我沈默沒說話,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嫉妒我才那樣說,但我也知道他說的也近乎是實情,可我這個條件也只能找到這樣“一般般”的女人了吧。
“普通”兩個字也可以換成“傳統”,她從小受到嚴格的家教,在很多事情上極爲保守。每當我試圖表示牽手或者接吻的時候,她都會一把把我推開,甚至反問我,“你怎麽會有那麽龌龊的想法?”我總是聽別人說有了女朋友就有了性生活,可是在她面前我連“做愛”這兩個字都不敢提,我生怕她會生氣。盡管摸不到親不到,但我心里還是挺欣慰的,能在這麽一個浮躁的大學還能找到這麽一個潔身自好的女性也是我的修來的福氣。
她答應與我交往的這兩個月的時光,可能是我這輩子最幸福的時光了吧,我們一起看電影,一起買冰淇淋,一起去遊樂場,一起在大學小樹林里面閑逛——每到夜晚,這里簡直成了發情地:熱吻的、互摸的、甚至打野戰的……
“那個女的手怎麽伸進她男朋友褲子里去了?”借著昏暗的燈光,女友看清了那兩個人的小動作。
“應該是在幫他撸管吧。”我試探著說。
“真惡心,光天化日下就敢做這種事。”她厭惡地說道。
“我的小公主,這都大晚上了,還光天化日?”
“你是不是也想這樣?”她語氣嚴肅起來,“我再次給你說清楚,我是絕對不會干這種事的。”
“沒有,真的沒有,我對你的愛絕對沒有那麽龌龊。”我趕緊對天發誓,然后加快腳步想要帶她離開這里,停留久了的話,她看不慣這些。
我倆走到學校后方的這個荷花池就停了下來,尋了張長椅坐下,晚風輕拂柳絮,姣白的月光照亮她臉龐,我忍住了強吻她的沖動,和她有一搭沒一搭的談論著今天課上所學的一些心理學的知識,逐漸說到了這個社會上流行的女權主義風氣,“女權主義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因爲任何社會關系都是社會生産力的反映……”我無顧忌地闡述著我的看法。
“打住!你這種也只是從宏觀上看的,你可以說整體上是這樣,但這個社會總有家庭在實踐女權主義啊?比如丈夫和妻子干同樣的家務,甚至有的嬰兒也是由丈夫帶大的啊?”她辯駁到。
我沒有還嘴,因爲她根本就沒在同一個頻道和我辯論,我在說整體,她在說個體。盡管我覺得她在答非所問,但我還是勉強地說道:“有道理。”
“你這就是在敷衍。”她似乎在這個問題上來勁了,“不管怎樣,我今后成家了就要實現女權。”
“好的好的,我都答應你。”我哪里想得到,我今天的對她的敷衍竟會在今后一語成谶,以至于在未來帶給我難以名狀的快樂和痛苦,這都是后話了……
快樂時光總是短暫的——這句話放在哪里都不爲過。隨著我對她激情的褪去,感情趨于平淡之余,我的占有欲逐漸冒頭了,我想這可能是和我身高、見識、家庭背景等原因所導致的自卑有關。我開始對她患得患失,每當她有部門聚餐時,我會讓她給我拍視頻,好讓我看看是些什麽人;我也會問她QQ里面的這些男性好友是誰;我甚至會懷疑和她通話的她的父親是她的“干爹”……盡管我深深地知道像她這種乖乖女壓根就沒想過出軌,可我還是壓不住我的控制欲和懷疑感,如同強迫症似的不斷地問她。剛開始她還會稍顯熱枕的回答我,好讓我寬心,但到后來,回答的越來越敷衍,直到刻意不接我電話或者直接對我反唇相譏。
“都2015年了,你以爲我是你家的丫鬟嗎?什麽都要管?”她憤怒地回答道。
“我就只是想問下他是誰,我沒有任何懷疑你的意思啊?”
“你不是懷疑我,那你問這個干什麽?我都已經給你說了很多次了,這個人是我社長,你還要我怎麽說?他長得像豬一樣,我也會和他好?我是在給他彙報外聯部的工作啊!不相信我就分手啊?”這是她第一次說出“分手”兩個字。
“分手就分手,我怕你?”我無所謂地回答道,帶著勝利的姿態離去了。我的背后,只聽到一陣嗚咽聲和秋風的怒吼,我始終沒有回頭。“她遲早會求我複合的。”我安慰著自己。
在那一刻,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勝利者,但回到宿舍后,卻又感到一點點落寞——如同小孩子失去了他心愛的玩具。她是我的初戀,我也是她的初戀,沒想到我的第一段感情居然這麽快就結束了,到底是我沒做好還是她沒做好?我捏了捏我脖子上的一個特別小的水晶球飾品,那里面嵌有一粒米,米上刻了三個字,是她的名字:
李子君。
“砰!”強勁的秋風把門重重地關上,“冬天快來了。”舍友不無感慨地說道。
“是啊,冬天快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