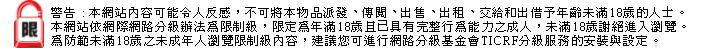借種(1-6)
(一)
頭頂的太陽象個火盆,烘烤著整個劉家村。麥杆失去了水分枯黃地伏在大場上,水牛不停地轉動,麥杆在石滾下發“噼噼”的響聲。
柱子戴著沒頂的草帽,手裏拿著一根趕牛的鞭子,緊尾在牛屁股後邊轉動,嘴裏不停地哼哈著趕牛的“擂擂”。光著上身的肌膚被陽光曬得油亮,汗水從他黝黑而又結實的後背滾下,褲腰已被滾下的汗水濕透。
“叔!牛不動了。”柱子擡頭一看,拐子爺立在牛前。
拐子爺是柱子的二叔,那年爲人家蓋房,從房頂摔下摔傷了腿。從那以後,人們都叫他拐子爺,漸漸地忘卻了他的大名。
“柱子,吃了沒?”拐子爺叭嗒著旱煙,濃眉下面眯著一雙小眼睛問著。
“還沒哩!”
“我叫你嬸爲你做點兒。”
“不了,葉蘭兒說她馬上送來。”
“柱子呀,你沒爹沒娘的,要學會自個兒照顧自個兒,懂嗎!”
柱子點了點頭,說他懂。
柱子爹娘死得早,那年他才六歲,爹娘夏季趕集,上了西河口的渡船,由于超載渡船翻了個底朝天,爹娘溺死。跟二叔手下成人,現在長大了又單過起來。依然住著那二間土屋。
“娘,我去麥場啦!”葉蘭兒提著籃子,籃子裏放著玉米餅與瓦罐,罐內是做好的菜湯。
葉蘭兒的公爹放下手裏揚場的木鍁說:“蘭兒,你讓柱子快爽些,地裏還有幾畝沒收哩。”
“爹,我懂了。”葉蘭兒應了聲,就急急地去了。
葉蘭兒的公爹劉大海望著離去的兒媳長長地歎了一聲:“哎!”
老伴王玉珍望了一眼,隨口問他,又怎麽了。
劉大海說,都過門二年多了就這麽下去怎麽得了,楞占個坑。
王玉珍告訴劉大海,說不是葉蘭兒的事,可能是他那獨種疙瘩來旺不行,她暗地裏注意了,人家葉蘭兒每月都來紅的。
葉蘭兒到了,在場邊的槐樹下拿出碗筷。向場上的柱子喊道,柱子,吃午飯了。
柱子聽了應聲說,好哩!我把牛趕邊上去,防止它屙場。
柱子喝起湯來象水牛飲水,葉蘭兒見他臉上的汗如同豆粒滾下,忙從自已的脖子上拽下毛巾遞給柱子。
(二)
柱子坐在樹下,吃起那玉米餅如同是山珍海味一般。葉蘭兒從地上撿起牛鞭子,說讓柱子歇會兒,她趕牛打起場來。牛好象不聽葉蘭兒的使喚,轉著轉著就轉到場心不動了,她便豎起鞭子要抽打水牛。
坐在樹下的柱子見狀,便哈哈地大笑起來。行啦,別讓鞭梢子抽著自個兒,你那細皮嫩肉的會起泡子。
葉蘭兒扔下鞭子,生氣地說,你是心疼水牛哩還是心疼我哩。
柱子聽罷,隻是嘿嘿的一笑,滿臉通紅。
柱子打場,葉蘭兒就在邊上不停地用鐵钗翻著麥子。太陽雖然偏西卻顯得依然火熱,那藍花圓領衫已被汗水濕透,緊緊地裹著她的身子。
“你歇會兒吧!”柱子打好了麥子,把牛趕出場外卸下石滾子。
葉蘭兒感到衣衫粘在身上怪不舒服,用手捏起胸前的衣衫不停地抖動。她擡頭看了一眼柱子,看到柱子向她望來,便停下手來不再抖動,嘴裏低聲念道:不害臊哩,念完就轉過身去。
柱子收回目光,說讓葉蘭兒回去,叫來旺把牛車拉來。現在有風,柱子要揚麥子了,揚好後裝進袋子好運回去。
柱子在來旺家吃了晚飯,去了東溝裏洗了回澡便回去了。夏日的蚊子在夜裏就嗡嗡地飛起來,柱子抱些麥杆點燃,又弄熄火苗用麥杆煙熏趕蚊子。柱子扔一張涼席在地上,在席子邊塞了些麥杆就算是枕頭了,睡下不一會兒便鼾聲如雷。
柱子走後,葉蘭兒收拾好碗筷便也上床了。來旺象往日一樣,上床隻睡他的覺。葉蘭兒掀開蚊帳舉起手裏的油燈,用燈頭小小的火苗去熏烤帳內的蚊子。她看了眼來旺,歎了一聲長氣便吹滅了油燈。
葉蘭兒的公爹劉大海又叭嗒起旱煙來,王玉珍用手中的芭蕉扇狠狠地在他肩上拍了下,說死老鬼啊,要抽煙就下床去抽,你看看咱家的帳子。
劉大海吐出煙霧,擡頭看了一眼蚊帳,白白的紗布帳子已經發黃了,的確增添了不少藍一塊青一塊的補丁。
劉大海下床,就坐在床頭的闆凳子依然抽著他的旱煙。半晌才把煙鍋底在凳子邊上敲滅了旱煙。
“來旺他娘,你問來旺了嗎?”
“問了又咋樣,人家葉蘭兒還是黃花閨女哩!”老伴王玉珍歎了口氣,手裏的扇子還在輕輕地搖晃著。
劉大海又裝了袋旱煙,嘴唇不停地叭嗒,煙鍋上的火苗也隨之閃動著。
“他娘呀!我倆對不起劉氏的祖宗喲!看來我們家要斷孫絕後了。”
“你讓我咋辦?”王玉珍在帳內回應道。
“來旺他娘,我看這樣……行不?”
(三)
劉大海這主意好象是想得很成熟才說出來的,一雙老眼還滲出點淚來。
王玉珍轉了個身子,把屁股轉向床裏臉對著劉大海,說你真能想得出來?這男女之事一旦發生了你還能行得住嗎?
劉大海放下煙杆進入帳內,輕聲地對王玉珍說,那長時間下去你就能保得住她不飛嗎。
老伴王玉珍點了點頭,說的也是喲!死老鬼,你說葉蘭兒她能肯嗎?
劉大海接過王玉珍手中的扇子爲她不停地扇著,這攬子事得要你出馬對她說去,聽到沒?我做公爹的可不好張這口喲。
王玉珍從床上坐起來,一臉認真的樣子,那你說,就是葉蘭兒同意了柱子能同意嗎?
劉大海的扇子停了下來,說要不是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你看他那熊樣,孤兒無娘狗啃頭能有這份豔福,白送個女人睡睡還不肯?
王玉珍向劉大海翻了個白眼,雙手在他的胳膊上使勁在掐著。
天剛亮柱子就過來了,葉蘭兒起早做好了早飯,爲柱子盛了碗面粉糊糊。柱子象是三頓沒吃似的,一口氣喝了兩大藍邊碗,放下手裏的碗便拿起鐮刀去了麥地。
葉蘭兒收拾碗筷,婆婆王玉珍在屋外對來旺說,來旺呀,你還去割點牛草吧,田裏就不用你去了,你也不能做重活的。
來旺聽後便背個蒌子放把鐮刀走了,劉大海在自家的場上翻曬著打好的麥子。
王玉珍進入屋內,那張老臉象是一朵未綻開的花帶著不自然的笑意。我說蘭兒呀,娘想給你說點事兒。
葉蘭兒拿著涮鍋的把子,在陶盆裏不停地轉動著藍邊大碗。娘,有啥事您就說。
我……我我,王玉珍顯得吞吞吐吐。
娘,您說呀!葉蘭兒放好碗筷。
王玉珍思量一會兒說,蘭兒,你到我們劉家快兩年多了,你家公爹與娘想抱孫子啊!說完她向葉蘭兒深深地望了一眼。
葉蘭兒沈下臉來,一屁股落坐在闆凳上把頭低了下去,叫了聲娘……!
未等葉蘭兒說完,婆婆王玉珍面無表情眼裏還噙著淚花,蘭兒呀,娘是過來人娘懂,娘也是女人啊!苦著你了閨女,娘想放你走可娘不舍呀!象這樣好閨女往哪兒尋去。
葉蘭兒已成淚人,撲在她的懷裏痛哭,娘,我不走。
王玉珍緊緊地摟著葉蘭兒,蘭兒呀,人啊不能沒有子孫,沒有子孫呀到老就沒依沒靠孤苦零丁了,人言說得好啊,娶親生子養老送終喲!
娘,葉蘭兒又叫了聲娘,眼裏盡顯無奈與絕望。
王玉珍用手輕輕地推開葉蘭兒,閨女,娘知道你這兩年多熬過來不易,如今娘隻能出個下策了。
葉蘭兒睜大眼睛不解地問,娘,你想說什麽哩?
王玉珍看著葉蘭兒,向後退了一步說,閨女,請你與柱子給我們劉家續個香火吧,娘求你了娘給你跪下啦!
葉蘭兒撫起婆婆說,娘,這事兒……
(四)
我知道這事兒爲難蘭兒了,可娘無奈呀!若不是來旺無能,娘也不會如此。
葉蘭兒並沒有回答王玉珍個上下,隻是拿起鐮刀匆匆地走了。
柱子已割倒一大片麥子,見葉蘭兒來了,便直起腰闆用褂角在臉上擦了把汗水,葉蘭兒定神地看著柱子,她還真的沒有認真看過柱子。
柱子說,你這樣瞧我咋地?
葉蘭兒說歇會兒吧,別累著,來,給你毛巾。
柱子接過毛巾從臉到胸脯擦了個遍,隨手又把毛巾還給葉蘭兒說,你去捆紮麥把吧,等你捆完了這塊地的麥子我也就割到頭了。
葉蘭兒從地邊割倒的麥子捆起,不等她把麥子捆完,柱子已割到了地頭。柱子轉身回望看到葉蘭兒才捆好十幾捆麥子,便從那邊走過來。
葉蘭兒,你先歇會兒讓我來吧,說完柱子就捆起麥把。
我歇那門子呀,我剛來也不累的。她依然做她的。
柱子朝她嘿嘿一笑,葉蘭兒看到柱子站起來,她意識地低頭看了一下垂下的領口便轉過臉去。
麥把捆完了,柱子與葉蘭兒站起來直了直腰闆。從遠處吹來微微的涼風,就這點點的微風也能讓柱子感到無比的涼爽。
拐子爺拿著鐮刀背在身後,從地頭的埂上走過,柱子呀,不回去吃午飯呀?
柱子用那頂舊草帽當著扇子不停地扇著,叔!你先回吧,我這就回。
拐子爺調高了嗓門兒喊道,柱子,葉蘭家的收完了你自已的畝把地也收了吧,別盡做幫工了啊,天說來雨就來雨的。
叔,我懂,柱子也用大嗓門回應著。
葉蘭兒擡頭看一眼頭頂正中的太陽,知道該收工了。
她從地上拿起兩把鐮刀朝柱子說,回吧,天不早了。
柱子尾隨在她的身後,路過小灌渠柱子停下了,說葉蘭兒你先回我洗個澡喲,說完他沖下灌渠。
柱子象是下水的鴨子,在水裏不停地撲騰。葉蘭兒看他得意的樣子,便放下手裏的鐮刀,把脖子上的毛巾取下,說柱子你快點,我淘洗一下毛巾,淘洗完了你就上來呀。
葉蘭兒踩在水邊,一不小心就滑入渠中。這小灌渠的水並不深,還不到一人高的深度,可葉蘭兒不會遊泳,落入水中就六神無主了,在水裏慌亂地瞎撲騰起來。
柱子急忙沖前將她抱起,使勁地抱上岸邊。葉蘭兒嗆了幾口渠水,不停地咳嗽帶著嘔吐,柱子把她抱在懷中不停地問她,沒事吧,沒事吧葉蘭兒?竟忘記放葉蘭兒下來了。
葉蘭兒濕渌渌的身子躺在柱子的懷裏,有一種感覺,這種感覺是她婚後到現在從未有過的,讓她這顆女人的心跳得利害,血液也沸騰起來,還嗅到了一股強大的男人氣味,這種氣味是來旺身上所沒有的。
她記得,入洞房的第一夜,來旺象是遺失了什麽東西。在她的身上不停地尋找,剝開她的衣服用雙手在她的身子上到處收索,來旺伏在她的身上使勁地揉搓軟中帶硬的乳房,手指撥弄乳頭,在來旺的粗魯調逗下,葉蘭兒的乳頭變得堅硬腫脹,原本紅潤的乳尖此時更爲挺拔。
來旺急忙脫下了褲子,可他那裆中之物漲得猙獰可怕,他把那話兒朝葉蘭兒在未經過濕潤的陰道裏腰力起勁一捅,葉蘭兒大叫啊的一聲,眼淚湧了出來。兩手更是抓緊被單。任由來旺野蠻粗梗的撞擊,不到一分鍾,他便倒在她身上,聽到的是一聲歎息和入睡的呼噜聲。
葉蘭兒慢慢地睜開眼睛,仔細地打量著柱子,他那雙眼睛發出的光讓她的心感到發燙。她感覺到了什麽,猛然將右手從他胸脯厚厚的肌肉上拿開。
柱子這才緩過神來,輕輕地將葉蘭兒放下。
(五)
柱子放下葉蘭兒,滿臉通紅顯得有些尴尬,在他雙腳周圍與葉蘭兒一樣淋下一圈子的水。說真的,到現在柱子的心口仍然跳得利害,因爲這是他除母親之外第一次接觸女人的肉體,這種感受心裏說不出是什麽滋味。
王玉珍做好了午飯,看到葉蘭兒與柱子回來就把飯菜盛上。
葉蘭兒一言未語就進房裏去了,出來時已換了一身幹淨的衣服。坐在桌邊的來旺隨口問了句:咋的,落水了?
葉蘭兒瞪來旺一眼,說吃你的飯吧,飯塞不住你的嘴呀?
柱子在門口的井邊脫下上衣,打了桶井水把上衣淘洗一下,然後使勁地擰幹了水重又穿上。
劉大海聽到老伴的叫喊,來旺他爹,吃飯啦!便把煙杆挂在肩上進得屋來,翻著白眼瞟了一下葉蘭兒與柱子。
幾天下來,麥子收割上場也打完了。但是,這幾天對葉蘭兒來說簡直是一種煎熬,婆婆的要求對她來說,她無法做到。她難于啓齒對柱子說她要他做那事兒,她更沒有想過與不是自已的男人做那事兒。可她被柱子從水裏抱起睡在他的懷裏時,他滾燙的胸膛讓她感到是男人的一種力量,而女人所需要的那種幸福那種欲望,她卻無法得到。
天漸漸地黑了,蛙與蟋蟀和知了的叫鳴聲組成了夏日的夜曲。劉大海在竈後燒火,王玉珍在鍋台上忙碌,一道做起晚飯來。
“來旺他娘,大前天他倆兒全身濕渌渌的,你說……”
“燒你的火,別瞎猜。”王玉珍愛理不理。
“這事兒,咱也不好多問,隻有等葉蘭兒懷上才能知道。” 劉大海等在老伴嘴上,半天回他這麽幾句,要說的話象是一口要吐的痰又咽了回去,隻好轉換了話題。
“飯就要好了,這麽晚他倆咋還不回來?”
“你說的輕巧,象是城裏人似的,那好幾畝地的麥杆要堆五六個草堆的。” 劉大海被老伴這麽一說,也就不再言語了。
場上隻有最後一個草堆沒有堆完。柱子在場上钗著麥杆,葉蘭兒在草堆上用钗堆疊著,漸漸地已堆積有一個人高了,柱子向上钗葉蘭兒就在上邊用钗接著,終是堆完了。
葉蘭兒用毛巾擦了擦臉上的汗水,隨後將毛巾扔下給柱子。柱子在身上擦了幾把將毛巾挂在脖子上,說葉蘭兒,我和好稀泥遞給你將草堆的頂封一下。
葉蘭兒在草堆上嗯了聲,可這話音未落,她一不心小就從草堆上跌落下來,重重地壓在柱子的身上。
(六)
葉蘭兒落下,一些麥杆也滑落在她的身上,她的雙唇已接觸到柱子的嘴上,這一舉動隻是一瞬間的事兒。她想爬起,可那些麥杆使她無法立刻站立,她隻是做了個女人應有的害羞動作把臉蛋轉到一邊,錯過與柱子的目光對視。
此時的葉蘭兒,象是落入一種魔鏡。柱子的一股溫流已滲入她的體內,連同他的脈動她也能感覺出來。
人言道,惡由心生,如果不是婆婆提這個醒,如果不是天天睡在一個無動于衷的男人身邊,葉蘭兒不會有這個念頭。
一個婚後沈默兩年多的女人,用孤獨與寂寞的傷痛包裹自已靈與肉的欲動,終于在渴望得到的關口沖破那道理智低矮的牆。
她轉過臉來,把雙唇壓在柱子的嘴上不停地吻著,雙手緊緊地抱住柱子的脖子。
唔!柱子被葉蘭兒的主動親嘴嚇得魂飛魄散,此刻他驚得口不能言,目不能眨,癡癡看著鬓雲亂灑的葉蘭兒吻著自己,怦然心跳。
男人在性欲的潮水中完完整整是一座泥雕,經不住任何急流就會徹底松散。
雄性的本能讓柱子發出沖擊的信號,他如同一頭野獸開始瘋狂,他立即翻過身體,要徹底地征服葉蘭兒,把全身的力量傳遞給她。
葉蘭兒屏住呼吸,牙齒緊咬著下唇,緊緊地閉上眼睛,好象地球在這一刻也停止了轉動。柱子將她兩腿岔開,陰道自然會張開縫隙。
柱子瞄準時機,慢慢向她靠近,眼看著就要插入縫隙,葉蘭兒卻這時迎上,啵的一聲,剛好緊緊得把柱子的陽具吞沒,她興奮地將它夾在裏面活動。葉蘭兒爽得飛起,她感覺自己要上天了。
葉蘭兒緊箍柱子的脖子,兩腳夾在柱子的屁股上,仿佛在打樁一樣,柱子也樂得輕松。在葉蘭兒的動作下,柱子有些力不從心。
這樣的情況並沒有持續多久,葉蘭兒翻了個身,騎在柱子身上,柱子的雙手被葉蘭兒按在她的胸脯上揉搓撫摸,她不禁哼出了萎靡不振的呻吟聲。在她屁股撅起來的上下抛落,柱子的陽具始終沒有脫離她的小屄。
她蕩漾在女人的幸福之中,身體微弱的疼痛在柱子給她帶來的快感中漸漸地淹沒。
柱子抖落身上的麥杆,全身如同從水裏剛爬上來汗流滿身。葉蘭兒還睡在地上不動,如同死去一般。她感到全身發燙,是滿足之後的癱瘓。
“葉蘭兒,咱回去吧,這麽長時間了,大海叔定會來尋咱們的。”柱子說這話時,好象是一個字一個字吐出來的。
“柱子。”葉蘭兒從地上坐起來 “嗳!”
“你以後還想我嗎?”
柱子象是偷了一件自已喜愛的東西,不知是還給人家還是留下,沒有回答。
“柱子,咱問你話哩?”
柱子傻傻地點了點。
“隻要你喜歡咱,咱就天天給你。”
到達葉蘭兒家的路口,柱子將肩上的鐵钗交給葉蘭兒,說他回了。
葉蘭兒說,你不吃飯呀?柱子說他不餓。
葉蘭兒望了他一眼,說你吃生鐵啦,幹了半天的活還說不餓。
葉蘭兒拗不過他隻好獨自一人回家了,她知道,柱子這小子一定是心虛哩,才不敢來吃飯的。
葉蘭兒家的小狗聽到聲響,在門口大聲地汪汪起來,當葉蘭兒走近它它才搖動著尾巴不再咬叫,連蹦帶跳地迎上前去。
婆婆王玉珍聽到狗的咬叫聲便開門出屋,說,葉蘭兒回來啦,娘給你熱飯去。
葉蘭兒說,娘,你先去睡吧,我想先洗個澡。
王玉珍轉身回房了,房內很黑隻有劉大海的煙鍋在一閃一閃地亮著。
王玉珍上床奪過劉大海的煙杆說,抽,抽就知道抽,嗆死了。
她又抵了抵劉大海,說往裏挪挪。
王玉珍放下帳門,對上頭房的葉蘭兒叫了一聲:蘭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