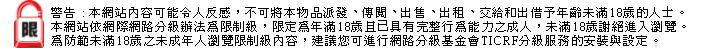梅蘭菊竹之「梅花,梅花,開了麼?」
『梅花,梅花,開了麼?』
窗外傳來中年男人嘶吼出的變了調的歌聲,刺耳的像是冬日里站在枝頭報喪的烏鴉。聽
到這聲音,我的動作頓了一下,然后又垂下頭,繼續整理著床上的衣物。
『你去啊,你這個婊子。你的姘頭又來找你了,你怎麽不去啊?你這個潘金蓮,別假惺
惺地在這裝了,我一時半會死不了,你不去,小心憋死你!』
沙啞的聲音,惡毒的咒罵,來自于坐在輪椅上的,我的丈夫。
我叫李春梅,我丈夫叫陸武男,與我同齡,亦是同鄉,窗外唱歌的男人是從小與我們一
起長起來的鄰居,趙有才。
我們三人從穿開襠褲時便相識,算是青梅竹馬,五六歲時一起入了村里唯一的小學,幾
年后又一起去了縣城讀中學。寒來暑往,生命的前十八年,都是綁在一起的。
年幼的時候,武男對我愛慕,無事時就會在我家窗外轉悠,喊唱著不知哪里學來的歌。
『梅花,梅花,開了麽?梅花,梅花,開了麽……』
每當這時候,我娘總是與我玩笑,說陸家這小子不把我家春梅娶走是不罷休呢!而我,
則是透過窗子,對著賣力地唱到臉紅脖子粗的他狠狠瞪上一眼,然后羞紅著臉垂下頭去繼續
做我的功課。
『陸武男!你又來這邊鬼嚎!還讓不讓人寫作業了!』
果然,過不多時,鄰家的趙有才就會沖出來,與武男打鬧成一團。我感受的到,他對我
同樣喜歡,但沒有武男那股子膽大直爽,從不敢當面對我表現什麽,只有在武男對我表示好
感的時候,假裝不經意地找出各種借口來搗亂。
『你趕緊出去吧,再不去,這倆毛小子要拆咱家房子哩!』
我的母親笑著與我說出這句話,然后,鄉村的田野、河邊,就留下三個小毛孩奔跑追逐、
嬉笑玩耍的身影。
幾年間,一直如此。
讀了中學,我逐漸懂了矜持,知道姑娘家和小夥子該做的、能做的事並不一樣,便少與
他倆瘋玩打鬧。但母親當日一語成箴,陸武男對我,愈來愈明顯地表露出了超出同鄉之誼與
同窗之情之外的意思,並緊追不舍。一開始,趙有才總在中間百般阻撓,但初中畢業后,他
由于沒能考上中專,回家務農,我與武男從此便只在假期返鄉時見得到他。
那時,我們成為了一對。
農村丫頭,嫁人永遠是首選,因此畢業之后,家里也沒了讓我繼續在外面闖的打算。武
男成績好,很快就找了份工地上的技術活,說好過段日子便去上班。與我回鄉后短暫停留了
一段日子,他便上門提親。兩家一向交好,彼此父母早已默認了我們的事情,很快就操辦了
婚宴,兩月之后,我和武男再次離家,踏上了外出務工的路程。
在外的日子雖然艱苦,但我們兩個都秉承著農村人特有的老實本分、踏實肯干,一步一
個腳印地走過來,生活倒也無虞。尤其在十九歲那年,我為武男生下第一個女兒之后,他更
是將我們母女視作他重于生命的責任,發了瘋一樣地工作,將整個家扛在肩頭前進。
那時候,努力了便會有回報。四年后,我們的第二個女兒出生,而武男已經成了工地上
一個小小的管事。又過了七年,在從不松懈的上進心的功勞下,他終于得到了一個經理的職
位。次年,我們也終于如願以償,生下了第三個孩子,也是唯一的兒子。
那時,已進中年的我,覺得所謂幸福美滿的生活也不過如此了。丈夫事業有成,兒女學
業優異,我賦閑在家,有保姆照顧生活起居,每天就是讀讀書、看看電視,人生如此,還有
什麽不滿足的呢?
然而,好景不長。變故在我們的第四個孩子將要誕生的時候突然襲來,我因為一次意外
的跌倒從樓梯滾落,陷入了失血性休克,幾乎斷送掉生命。當時武男正在一處工地視察,接
到電話后心慌意亂,一不小心從高高的腳手架上摔下。
最后,我有驚無險,母女平安。而我的丈夫,卻廢掉了半個身子。
人生最美滿,事業最巔峰的時候,卻忽然變成殘廢,不得以辦了退休,武男性情大變。
自那時起,原本溫和敦厚的丈夫,變成了一個脾氣暴躁、喜怒無常的男人。
那段時間,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一面要照顧年幼的孩子,一面還要小心著武男的
脾氣,隨時準備著迎接他的惡語相向。直到夜深人靜,丈夫孩子都已入睡,我才敢把臉埋在
被窩里,壓抑著聲音狠狠地痛哭一場。
這樣的生活,又持續了好久……
四十歲那年,大女兒夏蘭參加了工作,二女兒秋菊也如願考上了重點高中,兒子澤男進
入了縣城最好的初中,軍事化管理,食宿都在學校,一時間,我身上的擔子輕了許多,但武
男的脾氣仍不見好轉。深思熟慮之后,我決定帶著他和小女冬竹回到農村老家,遠離城市的
喧囂浮躁,希望鄉下的清新安詳能夠洗滌他的性子,讓他回到過去那個令人懷念的陸武男。
返鄉之后,見到了好久不見的趙有才。鄉村里安詳閑適的生活最不缺的就是流言蜚語、
家長里短。對我們一家發生的事情,他自然是早有耳聞,但見到我時,他的臉上,卻帶著一
絲不合時宜的欣喜。
畢竟曾是多年的至交好友,久別重逢的生疏幾日之后便消失不見,借著放心不下我們生
活不便的理由,趙有才開始頻繁出入我的家中。
隨著這幾十年社會的變遷,人們的心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拜金,已不是城市人家獨
有的想法。離家的這些年里,愈來愈多的鄉親們開始向外走,時不時就有誰家人在城里發了
財、當了官的消息傳回,那些有女兒閨中待嫁的家庭便一個個打起了小算盤,暗地里尋思著
誰家的小夥子看起來有前途,是個成為好女婿的料。這時候,雖然一表人才但是只懂種地的
趙有才就沒了市場,他又偏偏看不上那些願意下嫁但條件不行的姑娘,一年一年蹉跎下去,
高不成低不就,直到四十歲仍是老光棍一條。
對此,有才自己並不十分在意,父母又死得早,于是更沒人替他操心。歲月荏苒,原本
儀表堂堂的相貌也被時間摧殘的差不多,常年的田中勞作又使原本高大的他變得有些佝僂,
漸漸地,村里長輩教訓起自家好吃懶做的女兒時,開始用上了『再這樣下去,你就只能嫁給
趙有才』這樣的話。
可想而知,在這樣的境遇下,趙有才這些年的日子也並不好過。我也是回家一段時間后
才知道這許多事情,出于一種同病相憐的感受,對他當日見面時臉上那一抹欣喜,也便諒解
了。
換做是我,在被生活折磨到走投無路的時候,見到曾經一起度過無數快樂光陰的舊識,
也會是一樣的反應吧。
或許是不想在舊日情敵面前丟了面子,又或許多年沒有個可以交談的好友確實寂寞,陸
武男對趙有才竟是出人意料的善意,時不時便與他把酒言歡,談些陳年舊事,相顧唏噓,有
時痛哭,有時歡笑,整個人像是重新活過來一般。對此,我心中暗喜,亦默默期盼著趙有才
能多來做客。
但是,武男的脾氣並未因此收斂,尤其是酒氣上頭之后,每每對我呼來喝去,甚至因我
小小的疏忽而摔杯責罵。趙有才雖然勸阻,但畢竟是外人,說不上許多話,僅能在事后悄悄
安慰我幾句。某日夜里,武男又脾氣不順,沖我發起火,連我為他擦拭身體的水盆也打翻,
鬧大了動靜,隔壁的趙有才披著衣服風風火火地趕了過來。
家醜不外揚,雖然這壞事早已傳了千里,但外人進了屋,武男還是沒法繼續發作下去,
氣哼哼地讓我去準備酒菜,要趁著性子和趙有才喝一場。趙有才雖然覺得不合適,但也不放
心就此離去,便沒有攔阻。
這場酒一直喝到半夜三更,陸武男大醉著睡去。趙有才幫我將他擡到床上,收拾起桌上、
地上的狼藉。然后,在廚房里收拾碗筷的時候,他從身后抱住了我。
『春梅,你跟了我吧!』
酒氣混著熱氣呼一下噴到我耳根子上,我驚了一跳。他喝了不少,聲音也沒刻意壓著,
說出的話更是驚雷一般。還好,廚房與正屋離得遠,那邊沒什麽反應。
『老趙哥,你看你醉成什麽樣子了,說的什麽胡話!』
我呵斥著,用力將他推開。他卻在我面前撲通一下跪了下來。
『春梅,我喝了不少,可是我沒醉!我……我……』
他我了兩聲,卻說不出什麽來。而我呆了幾秒,連忙上前去攙扶他。
『老趙哥,這像什麽樣子!快起來!』
『不!我不起來!我……我唐突你了,我不是人!』
趙有才揮開了我的胳膊,開始狠狠地抽著自己的耳光。
『趙哥,你別這樣!一會讓老陸聽見……』
我不知所措地輕聲喊道。
『讓他聽見好了!』趙有才手上未停,向我哭喊,『春梅,陸武男對不起你!沒錯,他
有福氣,娶了你這朵咱村最美的花,但是他不知道珍惜!不知道把你捧在手上疼著愛著!你
看看他現在的樣子,他給不了你好日子過!你跟我,跟了我好不好?咱繼續養著他,咱一起
供冬竹念書,咱一起過好日子……』
『趙有才,你瘋了!』
顧不得可能會把武男吵醒,我顫抖著厲聲打斷了他。
『我……我……我沒瘋!』趙有才嘴唇抖了幾下,大聲喊起來,『你以為我這麽多
年是找不到媳婦嗎?不是!春梅,我是放不下你啊!小時候,我沒他陸武男膽大,做不出在
你家窗子外邊給你唱歌的事,但是我想啊!我也想那樣子站在那沖你唱,沖你笑,哪怕看見
你瞪我一眼也好啊,春梅……』
『別說了!』回想起那段恍如隔世的日子,我的眼淚也簌簌掉了下來,『以前的事,別
提了……』
『不!我要提!以前不敢跟你說的話,我現在跟你說。以前不敢對你唱的歌,我現在給
你唱!』說完這話,聲淚俱下的趙有才,跪在那里,仿佛瘋了一樣,扯開嗓子唱了起來。
『梅花,梅花,開了麽?梅花,梅花,開了麽……』
萬籟俱寂的深夜,只有這淒厲嘶啞的歌聲,回蕩在夜空之中……
我呆望著他,不知道該說什麽。這一刻,我多希望我的丈夫能醒來,醒來將他趕走,讓
我回到那雖然痛苦卻平靜的生活中。
梅花,梅花,開了麽?
歌聲中,趙有才站起了身子,一步步走到我跟前,把我抱住。
『春梅,我想你。這些年里,我天天想,夜夜想,我想見你,可是見不到。我怕你過得
不好,在外面受苦,可是我又怕你過得好,把我給忘了。春梅,我想你回來,等著你回來,
等了一年又一年,你回來了,真好,真好……』
『趙哥,別這樣,真的別這樣……』
我感受著男人的臉埋在我的頸間,潮濕的淚水順著我的發梢向下滑,自己的眼淚也忍不
住開始一串一串往下掉。
『春梅,哭一場吧,我知道你委屈。就算你不跟我,就這樣趴我肩上哭一場也好。從那
時候起,我就是個沒用的男人,我能給你的,也只有這個了啊!』
『嗚……』
心防決了堤。這些年的痛苦、委屈,全在他的這句話里爆發出來,我重重地在他寬闊的
背上拍打,狠狠地咬著他的肩膀,肆無忌憚地哭了出來……
那天晚上,我們什麽也沒發生,卻又明明發生了什麽。送走了趙有才,我和衣躺在陸武
男的身邊,聽著他如雷的鼾聲,怎麽也無法入睡。四十多年的人生像是電影一樣在我眼前放
映著,先是黑白的,慢慢變成彩色,又變成黑白,然后,又有了一點色彩……
第二天,一如既往地早早起來,做了早餐,送冬竹去上學。走到院門口的時候,這孩子
忽然回過身來,拉住我的衣袖。
『媽,你不要跟老趙叔走!』
一句話,像是一把刀子插進了心口。我空白著,對著小小的丫頭無邪的懇求的目光,什
麽也說不出來。
『媽,我什麽也不跟爸說,你別跟老趙叔走!』
淚水在冬竹的眼眶打轉,她雙手握著我的胳膊,用力地搖晃。
『放心,媽不走。』
我轉過頭去,不讓女兒看見我的眼淚,輕輕答應。
『嗯。』
得到我的保證,冬竹松了口氣,點了點頭,轉身離開了。而我,卻像是被一根繩勒住了
脖子,連呼吸都被梗在嗓子里,張大口,卻透不過氣來。
我忽然,很想念昨夜的那個肩膀。
『你個臭婆娘,死在外邊啦?還不快滾進來,老子要上茅房!』
屋子里傳來武男的叫罵,我連忙抹干淚水跑進去,伺候著他下床、如廁。
『老趙昨天晚上是不是在外邊唱歌啦?』
雙手端著盆,接著他自垂軟的下體噴出的腥臭尿液,我被他的話嚇得渾身一抖。昨晚,
他終究是聽到什麽了嗎?
『媽的!老子做夢都聽見他在外頭鬼嚎,也不知道在喊叫啥。年輕那會他就對你不安好
心,現在你都成老娘們了,他瞅你的眼神還那麽不對勁!你可得給老子小心點,別他媽出去
丟我的臉!』
武男一邊尿一邊不干不凈地罵著,卻似乎是不知道昨晚發生了什麽,我松下氣來。
『放心吧,我倆沒事。』
『沒事?現在沒事!老子現在不中用啦,日不了你,可不知道你能憋多久。我可是聽見
過你自己偷偷發浪!』
武男的起床氣越發越大,字字句句都戳中我的痛楚。傷了之后,他已不能人道,作為一
個正常的女人,這些年里,我終歸有些被欲望煎熬到無法自持的程度。我不敢在他面前表現
出來,怕會讓他自卑自棄,卻沒想到還是被他知道。
『咋啦?低著頭不吭聲是啥意思?以前在縣城你沒熟人只能自己弄,現在隔壁院子就有
個四十歲的老光棍,攢了不少貨呢,誰知道你會不會哪天憋不住了爬他家的�!』
他的話越來越難聽,我低著頭,等到那淅淅瀝瀝的水聲終于結束,捏著他的命根子抖了
兩下,端著尿盆走出屋子,逃離那毫不留情面的羞辱。
將尿倒進廁所,洗了盆子,門外響起有人推車賣豆腐的吆喝聲。我連忙打開院門想去買
塊豆腐,卻看到趙有才正站在自家門口愣愣地望著這邊。
眼神相對,我們同時張了張嘴,卻誰也沒說話。沈默了一會,我重新關上了大門。
該說什麽呢?我不知道。
也許他有著不顧一切的決心,也許我該掙脫身上的層層枷鎖,也許梅花應該在凋謝前美
麗地綻放一次……但是,我們都知道,那樣做的后果,叫無可挽回。
在夏蘭小的時候,我為她講過一個童話故事。里面說,所有的花朵,都是蝴蝶變成的。
那時候,夏蘭問我,為什麽蝴蝶要變成花?我回答:『因為蝴蝶只能飛來飛去,只有變成花
朵,才能安定下來啊。』
現在,我很想知道,為什麽蝴蝶要變成花?
日子在繼續。武男依舊暴戾,趙有才依舊常常在他的門前守望,冬竹則像是防止我逃跑
一般,總是跟在我身邊打轉。
有才仍會到我家來,但是面對的,是武男若有若無的敵意,冬竹明顯的提防,以及我刻
意的躲避。慢慢的,我見到他的次數少了下來。
不知不覺,時近端午。這天早上,我送冬竹出門,順便去買了大把蘆葦葉回來。雙手被
占滿,進了院子已經是氣喘籲籲,屋子里卻又一如既往地傳來武男的叫罵聲。我立刻扔下葉
子,跑進去伺候他起床撒尿。
淅瀝瀝瀝瀝……
黃色的尿液在盆里濺起水花,不斷有零星的液體灑在我的手背上。我一動不動地垂著頭,
麻木地聆聽著那個聲音由密集變得散亂。
『陸哥,春梅,我……』
當趙有才手提著一袋粽子推門而入的時候,看到的,就是我正在捉著武男的陽具抖去殘
留的尿液的景象。
『媽的你個臭婆娘!越活越回去了!連鎖門你都不知道!』
好面子的陸武男在這屈辱的時刻立即爆發,掀翻了我用一只手端著,本就顫顫巍巍的尿
盆。臭氣熏天的尿液當頭澆下,順著我的頭發形成一條條水柱滴落,趙有才在這突然的變故
中驚呆了。
『陸哥,你咋能這樣對春梅!』
愣了一下,趙有才立刻將粽子丟在地上奔了過來,不顧我身上的汙穢扶我起身,同時大
聲喝問。
『春梅?他媽的你知道把我叫哥,就不知道叫她一聲嫂子?趙有才啊趙有才,你果然對
她賊心不死!』
沒有絲毫愧疚,陸武男狠狠盯著我倆,仿佛他變成今天這樣,所有的錯都在我們身上一
樣。
『陸武男!你咋會變成這個樣子!』
趙有才滿臉的不可置信。他知道武男的脾性變壞了,卻從沒見到過他如此惡劣的樣子。
『我他媽變成什麽樣關你屁事!你瞪啥瞪?你想做啥?老子教訓老婆還要你插手啦?』
武男望著瞪大眼睛喘著粗氣的趙有才,臉上全是不屑和挑釁。
『好,好,陸武男,你真行!春梅,跟我走!』
趙有才氣得渾身打顫,抓著我的手就往門外走去。
『趙哥,你別……』
我掙扎著,他的手卻像鐵鉗一般狠狠攥著我的手腕,帶給我鉆心的疼痛。
記憶中,他總是在任何場合保護著我,一起出去玩的時候,有他在,連夏夜的蚊子也近
不了我的身。現在的他,已經憤怒的失去了理智,否則,是絕不會這樣用力地握痛我的。
是啊,一切都是為了我……
我沒再說話,默默地跟著趙有才走出了屋子。
『他媽的!我就知道你們不是好東西!狗男女!淫娃蕩婦!你們他媽的滾!滾的越遠越
好!一輩子也別回來!!!』
身后,陸武男的叫罵聲不絕于耳,但此刻,我只感受到手腕上的痛。鉆心的,安心的痛。
我們沒有滾的很遠,就進了隔壁趙有才的院子。
到了房里,他才驚覺到我的手腕已經被握出腫印,忙不叠地放開我的手,不住道歉。
『沒事。』
我低聲說了一句。然后,誰也不知道該說什麽。
『我,我去給你燒水,你先洗洗。』
看我的頭發仍濕漉漉的,趙有才念叨著,起身出了屋。剛剛他身上感受得到可以為我殺
了我丈夫的勇氣,而此刻,他卻連我的眼睛也不敢看一眼。
我身上汙穢,不敢坐下,就站在那里打量著屋里的陳設,四處都十分簡陋,唯獨當中的
桌子上擺放了一堆沒用完的糯米、紅棗和粽子葉十分的醒目。不多一會,趙有才端了一大盆
熱水進來,又去拿了毛巾、香皂,和一身換洗的衣服。
『我這只有男人衣服,你將就一下,先洗干凈再說,我去外面,水不夠就叫我。』
他囁囁嚅嚅地說完,又退了出去。
『嗯。』
我輕應一聲,也不知他是否聽見。門被關上,開始脫去身上的衣服,就著熱水,一點一
點清洗著自己的身體。
二十年前還光滑幼嫩的肌膚,在這些年里早已變得松弛、粗糙、還有幾處瘡疤。小腹上
一道長長的疤痕是生冬竹留下來的。由于武男出事,生過這最后一胎,我連月子都沒做,身
上落下不少病根,女人該有的資本,也幾乎已經全都喪失了。
陸武男說的沒錯,都已經是老娘們了啊。
這樣的身體,這樣的我,還有什麽值得他迷戀的呢?
『老趙,我好了。』
沖門外輕喚了一聲,我透過窗子,看到趙有才把手上的抽了一半的煙扔在地上踩滅,起
身走來。
我沒有拉窗簾,但是他始終都蹲在窗外,不曾回頭看一眼。
『春梅,你……』
『怎麽了?你不是說讓我跟了你嗎?怎麽現在又這表情?』
我用玩笑掩飾著自己的不自然。第一次在陸武男以外的男人面前赤身露體,我的心情是
忐忑的。我甚至都不明白自己為什麽要這樣做。
『春梅,我……』
『你除了春梅、你、我,就不會說別的字了嗎?』
我一步一步向他走進,抓起他的手,放在我的胸脯上。
那里下垂的很厲害,早不復當年的飽滿堅挺,但趙有才看向那里的目光卻無比虔誠,虔
誠的讓我內疚。
『對不起,老趙,我已經不漂亮了。』
我喟嘆。
『不,春梅,你永遠是咱村里,不對,是全天下最漂亮的一朵花!』
嘴上說著,他的手卻好像放在針氈上,一動也不敢動。
『撲哧!』我笑出聲來,『還記得那會,你叫我小梅花,我叫你趙沒才,到了現在,你
叫我春梅,我叫你老趙。一切都變了。』
『有些事,不會變的。』
趙有才的手終于動了,卻是離開了我的胸,輕撫著我的臉頰。
『什麽都會變的。』
我笑著堅持。
『不,不會變的。』
他也笑了起來,緊緊抱住了我。
愛撫、親吻……
很多年后,我再次嘗試到了這種滋味。雖然是來自于另一個男人,我卻無比的心甘情願。
『春梅,你永遠是我心里的小梅花,寒冬臘月也開不敗的最美的小梅花,不會變的。』
呢喃著,那些年總是跟在我身后,在遇到危險時又會立刻沖到我身前的男孩,進入了我
的身體。
『你知道嗎?春梅,那時候我就跟自己說,這輩子,我只有李春梅一個女人。』
輕柔又灼熱的話語在耳邊蕩漾著,我的手撫上了他的背,雙腿纏上了他的腰。我知道,
在這一刻,賤貨、蕩婦、下賤、不要臉……這些字眼都將永遠背負在我的肩上,但是我清
晰地聽到自己的心在說:我,不后悔。
老趙的每一道皺紋都在訴說著幸福,每一次喘息都透露著滿足,每一下沖刺都好像要把
全部的心意送進我的身體。我放肆地叫著,叫出已經十幾年沒有發出過的聲音,叫出心底所
有的不甘與委屈。
武男說的沒錯,這老光棍確實是攢了不少存貨,又是個童男,沒一會就在我身子里交了
槍。我撫摸著他脖子后面因為常年勞作鼓起的大包,笑著說他老了,不中用了。然后他賭著
氣又來了一次,但同樣沒多久便又敗下陣來,換來我更加開心的嘲弄。
玩笑,打鬧。兩個四十多歲的人卻像是一對孩子,相擁著,赤裸著,一起回憶著以往的
種種。即使說到嗓子啞了,也那樣凝望著彼此,不離開一分一秒。
我知道,這件事情對我來說,無關于欲望,無關于愛情,只是一場投降,投降于現實。
我向生活卑躬屈膝,承認我已經堅持不下去,承認我已經放縱了自己,把自己交給命運去隨
意地處理……
我知道,在這短暫的幸福過后,我的生活就會暗無天日。
只是,對不起了身上這個男人。
終究是要有結束的時候。當我穿著趙有才的衣服,緩緩地扒開門閂,拉開大門的時候。
我想,我也許再也不會走進這個院子,見到這個男人了。
身后的趙有才沒有說話,但我感受得到他留戀的目光。我總歸不是個果斷的女人,沒辦
法拋下一切,只有這唯一的一次,是我自己的逃避,也是對他的報答。
吱呀……
兩扇門,緩緩地分開。在我面前的,是坐在輪椅上冷著臉一言不發的陸武男,還有站在
他身后,滿臉都是眼淚的我的女兒。
『媽……』
見到我,冬竹的臉上閃過一抹笑,但立刻被委屈和責怪所替代。同時,趙有才的身影又
沖到我的面前,對著我的丈夫跪了下去。
『陸哥,是我逼她的,你要殺要剮都沖我來吧,別為難嫂子!』
他沒有想到陸武男會守在門口,只是像過去一樣,習慣性地沖出來保護我。即使已經相
隔十幾年,這習慣卻依然沒變。原來有些事,是真的不會變的。
加上第一次知道我和武男成為一對那一次,這是他第二次稱呼我為嫂子。
『壞蛋!』
早已抓在冬竹手上的半截磚頭飛了出去,落在趙有才的額角上,血流如注。
『不準你搶我媽媽!』
冬竹又撿起一塊石頭丟了過去。陸武男注視著我,一句話都沒有說。圍觀的人逐漸多了
起來,他環顧一周,從輪椅里抽出一根藤條。
『跪下。』
他冷冷說了一聲,我沒有反抗,繞過趙有才,走到武男面前,下跪。
啪!
第一下就直接抽在了我的臉上,火燒一般的疼痛,溫熱的血液霎時流到嘴角。
『爸……爸!你別打我媽,都是趙叔的錯,你別打我媽啊……』
冬竹愣了一下,立刻哭叫著撲向陸武男,去奪他手里的藤條。同時,趙有才又沖過來,
護在了我的身前,與陸武男面對面對峙著。
『老趙,把冬竹帶到一邊去。』
我嘆口氣,對著面前佝僂卻寬闊的脊背說。他回過頭,深深地望了我一眼,我沒說話,
我知道他能懂。
趙有才站起身,將掙扎哭鬧的冬竹抱起,任由小女孩鋒利的指甲在他臉上留下一道道血
痕,緩緩地走到了一邊。
啪!
第二下抽打,狠狠地落在我的額頭上。
啪!
啪!
啪!
……
一下一下,鉆心刺骨,撕心裂肺的痛。
圍觀的鄉親們指指點點,卻沒人敢勸阻。這個村子已經好久沒有這樣靜過,只有小女孩
的哭叫和藤條的抽打聲……
窗外的歌聲猶自傳來,丈夫的咒罵猶自不停。我收拾著衣物,不說一句話。
臉上,手上的傷口都已經結了痂,開始慢慢地脫落。只是那痕跡,可能永遠也不會消失
了吧。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蝴蝶為什麽要變成花,也不知道梅花為什麽要在寒冬里倔強的開放。我只是現
在才發現,未必長久的就是美好,也許有的時候,凋謝,才是安寧。
行李終于裝點完畢,夏蘭的車也已經到了門口。我們沈默著,上車,離開,駛過趙有才
的家門,駛出村口。
后視鏡里的公路逐漸地弄成一條細線,再也看不到那個孤零零的身影,只有一句句嘶啞
的歌聲,仿佛依舊縈繞在耳邊。
梅花,梅花,開了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