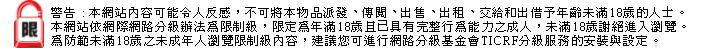國 賊 1-6
一雙照樓頭老去身,一生分作兩回人。河山半壁猶存末,松檜千年恥姓秦。
翰苑才華憐俊主,英雄肝膽惜昆侖。引刀未遂平生志,慚愧頭顱白髮新。《文子
書》—陳小翠題汪兆銘
一、初見
「一個圓滾滾,黑乎乎,個頭可能才過我腰的女孩激動的拿著《民報》對我
說,您就是精衛先生麼?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樣。我心下不喜,低頭緩步向路內側
繞去,可她蹦蹦跳跳的攔住我的去路。只是我沒想到,這一攔,就是一輩子。」
汪兆銘說(汪兆銘,字季新,筆名精衛。因文色出彩,世人常稱其為汪精衛)。
一九零七年三月 初春 喬治市
陳耕基回家時,璧君正在院內的躺椅上小憩,他看到女兒酣眠的樣子不由微
微一笑,悄聲從她身邊繞過,把手中的「進步」報紙輕輕放在了院中的石桌上。
廚娘正待問老爺好,卻被他攔住,低聲吩咐下去:「飯得了沒?沒得的話加一道
香菇燜豬肉,環兒喜歡吃。」繼而進了屋徑直上樓更衣去。
等廚房逸出一陣醬香味時,璧君醒了,肉呼呼的小手揉揉眼睛環顧四周,而
後眼前一亮搖晃著身子來到石桌前。是《民報》,隨著攤開報紙的動作,她雙臂
上的肥肉跟著抖了兩下,「精衛,精衛,是了!在這裡。」
《論革命之趨勢》,幫側一行小字注道「此文雖乃舊文,但三民主義思想為
新……」她津津有味的淺聲誦讀著,這些聞所未聞的思想與平日裡先生說教截然
不同,看著新鮮的同時又不免為行文流暢,辭藻優美暗暗喝一聲彩。怎樣的人才
才能寫出這般令人血脈僨張的句子?
她支起了下巴,開始幻想起那個叫精衛的作者的樣子。這般博古通今,引經
據典的,必定是上了年紀的人,也許還留過洋,兩鬢斑白就和爹一樣,但肯定沒
爹胖,必是一副瘦弱的文人樣子……腦海這天馬行空被傭人請吃飯打斷,她不開
心的皺了皺扁平的小鼻子起身往飯廳走去。
席上娘不在,爹暗沈著一張臉,兄長示意璧君別說話安靜的吃。她拿眼剜了
他一下,著傭人拿了兩個空碗,滿當當的乘了些飯菜,用託盤托著上了樓。
推門軟語勸了好一陣,娘才放下板著的面孔對她說:「環兒啊,你爹最近總
往那個什麼新籌的同盟會跑就算了,今兒還捐了一大筆款子。我看那些所謂的革
命人士一定都不是什麼好東西。」
她掩嘴笑了笑道:「娘,您先吃吃塊人參雞,這可是姥爺鋪子裡新進的野山
參煲的。你不吃不辜負了他老人家一番美意不是?而且為置氣傷了身子什麼的多
不值當。您說的有理,咱家雖不缺錢,但也不能讓人白騙了去不是?我聽聞那個
同盟會明天會有演講,到時候我和爹同去看看他們有幾頭幾臂,您是知道我
的……」
衛月朗聽到女兒這番話這才轉怒為喜,說:「就你個丫頭會說話。對了,明
兒你回來路上去趟你姥爺鋪子,給我抓幾附安神藥。最近啊,我總是心緒不寧的。
前些日子你舅媽還跟我誇你來著,說你寫的那個安神方子比店裡常駐的孫頭開的
還管用。」她說罷,便敞懷吃將起來。
是日清晨,陳璧君也不打扮,梳洗完畢隨便披了件衣服,把頭髮向後攏了攏,
就跟著爹去了街上。陳耕基是商會會長,沿途不少熟人,光是打招呼就用了半晌。
等到了演講的廣場,那裡已是人頭湧動。她遠遠瞥見臨時搭起來的檯子上站著個
模糊的人影,可還沒看仔細便被爹拉到一旁:「環兒走,隨爹去見過幾位先生。」
等父女倆好容易穿過人群到台下時,演講卻已開始。
清亮的嗓音令她心神一震,忙抬頭看去,一襲白衣入眼,就再也沒能使她移
開目光。他的眉梢神氣的上揚,眼中神采似浩瀚星河,鼻直口方,雙唇開合間都
是那些報刊上提及的新式道理,字字鏗鏘,條理清晰。陳璧君看得不能自已,不
由高呼一聲「好」,人群似被帶動,叫好聲此起彼伏,而後匯成了雷動般的掌聲。
臺上的青年頭微微歪向一邊,打量著台下那個第一個開口叫好的女孩。
璧君與他對視數秒,看到,他笑了。這一笑真如書中所言,可以融冰,可以
攝魂,短短數息間,她的心中竟轉過數百個念,這世間怎會有如此妙人?忙抓住
爹的袖口問道:「他是誰?」
陳耕基被女兒猛扯一下沒反應過來,愣了一下答:「這小夥子好像叫汪兆銘。」
見女兒還沒鬆手又補了一句:「就是你常看報上寫文的那個精衛。」袖口瞬間被
丟開,他還沒鬆口氣,就見女兒突然雙手捂面,嬌羞的呀了一身,扭頭便跑。他
有些懵,而這時臺上又換了個人,還沒開講便先謝過陳老闆的慷慨解囊。眾人的
目光都聚在了他身上,一種自豪之情油然而生,也就忘了女兒為啥突然耍小性子
跑掉的事。
這幾日衛月朗發現環兒變了,變得愛漂亮了。從不施粉黛的她居然買了一兜
子胭脂水粉,沒事也不讀書看報了,就坐在房間裡對鏡塗抹,還請了祥興號的老
闆上門量身定做了好些衣裳。
一定是有心上人了,衛月朗暗想,卻也不去打探,這丫頭臉子急是出了名的。
陳璧君這幾天過的喜憂參半,喜得是那汪哥哥一表人才,無論學識還是外形
都讓她不能自已,憂的卻是那次聽講時自己居然就這清水面孔的去了,也沒好好
打扮一下失了禮。
他對我那一笑,哦,想到這裡,她心神不由一漾,手下抹粉的速度又快了幾
分,好不容易纏著爹許下帶自己去同盟會,這次一定要以最美的樣子見到汪哥哥。
月白的旗袍靜靜的掛在她身後的架子上,被窗外的風吹起,蕩。
想像總是美好,而現實卻是相去甚遠。陳璧君好不容易擠進了月白色的旗袍,
她渾圓的臂膀盡數露在袖外,肚腩被貼身的緊致勒成了三圈,連呼吸都變得有些
困難了起來。可鏡裡的妝容是喜的,白裡透著粉,眉是翠的,上飄,唇是紅的,
半點。眉心耍了心機用金筆描了個圖樣,後又覺太繁複徒手抹了去。此時聽見爹
在樓下喚出發,她忙攏好頭髮,三步並成兩步下了樓。
會席間,風姿卓越者眾多,可在陳璧君的眼裡,哪怕是逸仙先生也被那個叫
汪兆銘的年輕人比了下去。與臺上的口若懸河不同的是,他話不多,常常在話題
間陷入沈思,可出聲時往往是語驚四座,晨光從窗格裡印在他的面上,使他整個
人都亮了起來。散會後,她見汪兆銘從側門出,便急忙追了上去,臨行前沒忘從
報架上拿起一刊《民報》。
汪兆銘這一路走的很慢,想著家國社稷,不由幽幽歎了口氣。不料說時遲那
時快,一道黑影堵在了身前,他定神卻沒見著身前有人,剛想抬步又覺不對,低
頭才見一個圓滾滾,黑乎乎,個頭可能才過他腰的女孩。女孩仰起頭,肉嘟嘟的
臉膛上堆滿了笑,手中的《民報》被攥的呼啦亂響,激動的聲音都有些顫抖了:
「您就是精衛先生麼?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樣。」
少女懷春的多情樣兒油膩膩的漾在了臉上,只把他看得是心裡一毛,抵觸之
情驟升,抬步便想繞過去。可陳璧君怎容得自己朝思暮想的人兒就這麼逃走,肉
臂一橫,側步伸手攔住了他的去路。
也不枉她這些年來在學堂受的薰陶,急智還是有些,攤開了手中的報紙,指
著那篇《論革命之趨勢》把前幾日心中對此文的不解之處一股腦的問了出來。汪
兆銘起初頗有些不耐,但隨著交談發現這丫頭人雖小,卻對革命有著自己獨道的
見解,不由收起了小覷之心,認真的解答了起來。
兩人興起,當街聊了半個時辰,汪兆銘知道了她是慷慨義士陳老闆的次女後,
態度變得越發客氣了起來,而陳璧君則旁敲側擊打探到了他行四,當下懷著小心
思改口叫了四哥。
只可惜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汪兆銘此等精明的人怎會瞅不見這小女生眼裡
那明顯的愛慕之意,直白的告訴她自己已有婚約。見著陳璧君跟打了霜的茄子瞬
間蔫下去的樣子,他不由在心裡暗暗歎了口氣,說聲抱歉,抽身走了開去。陳璧
君一人在街上站了許久,手中的報紙滑落在腳面,她向前走了幾步,突然又回身,
把報紙撿起來,像揣寶貝似的緊緊護在胸前。
回家後她脫了衣服躺在床上,傭人叫吃飯也不答應,渾渾噩噩的睡,等再轉
醒時暮色已經籠了一切,只有窗外微微的月光透了進來帶著些許亮。枕邊的報紙
皺巴巴的團成一團,她細心的將它攤開,指尖一遍遍抹過,油墨散出了若有似無
的香。想著白日裡四哥的笑貌音容,她心裡蕩漾了起來,指尖從報紙慢慢滑向自
己,身子後傾,仰躺。
帶著油墨味兒的手指在乳尖滑過,一遍,兩遍,身子跟著熱了起來,本是光
滑細膩的乳暈,緊緊縮皺成一團,簇擁著柔嫩的乳尖變得堅挺。她的皮膚不夠白
皙,可年輕的身子卻透著一股子活力。
而現下這股子活力隨著她的手在身上迅速的遊走,從大而扁的乳房,到深深
凹陷的肚臍,再到黑濃草叢裡,那粒縮皺在皮肉裡的嫩紅。水就這樣從穴道裡向
外湧,透明,粘滑。手指沾著淫水上挑,先壓後揉,嫩紅迅速充斥著血,從皮肉
裡掙紮而出。
她本抓緊著床單的另一隻手捂住了自己的口鼻,怕出聲所以用了些力氣,逐
漸稀薄的氧氣使大腦裡出現了短暫的空白,指縫裡逸出吱哇亂叫的聲,雙腿劇烈
的抖動著,床板發出砰砰的聲響,所有的氣力都隨著氧氣被抽走,只剩下那一絲
微薄的力量在腿間那一點,蓄力,凝聚,再噴發……
她倒在濕漉漉的床單裡抽搐,肥胖的四肢不時的抖起幾層肉波,雙眼翻白,
失去了神采。而後她深深的抽了一口氣,面色才暈了紅。
她的嘴角上揚,滿足的伸舌潤了潤唇,剛才在極樂的須臾間,自己見到了四
哥哥和他溫柔的目光。
她翻過身去,清冷的月光下,豐滿的屁股蛋上映著幽幽的水光。
當夜這年方二八的姑娘在心下發了願,這一世她定要那四哥哥全身心的屬於
自己。